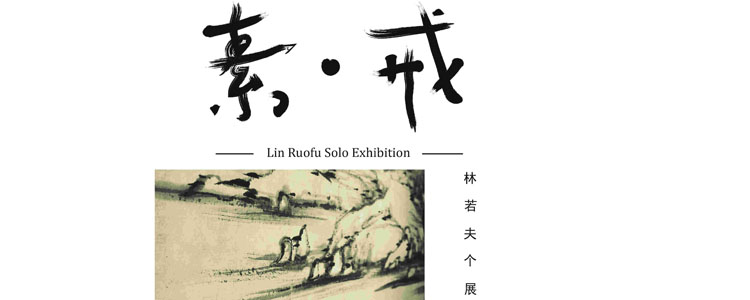
佛学在唐代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成果:一是经典研究领先全世界;二是教义的研究走向中国化。
南朝梁代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印度高僧菩提达摩由海路来华,在广州登岸,不久即应邀北上金陵与梁武帝会晤,后因见机不合,达摩旋往嵩山少林弘法。达摩在印度是禅宗的“西天第二十八祖”,来华后创立门户,被后人尊为中土禅宗的初祖。禅宗的“血脉”传到第五祖弘忍,宗门仍未能振起,事业平平而已。唐咸亨年间,慧能在弘忍的激赏之下获得了法嗣的衣钵,是为六祖,那时慧能才30出头。16年后,回到南方的慧能开始弘法。
慧能是一位敢想敢说敢干的宗教改革家。相传他的文化程度很不高,但其“夙慧”极深,思想十分新锐。当年弘忍放下一大群追随了十几年的门下弟子而将祖衣传给才认识了八个月的一介岭南樵夫,正是看出在他身上蕴藏着惊人的智慧与胆略,且料定此人日后必能大振门风。作为接班人,慧能果然不负师望,他开创了“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又立下了农禅并重的宗规,禅宗遂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样板。仅仅几十年的功夫,南禅的声势席卷天下,不但弹压了北禅,还亮出欲令他宗让出一头地的气派。自此,“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南禅取得了中国禅宗法统的正宗位置。
禅宗是一桩十分庞杂而深邃的历史文化现象。自唐代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处处都可找到禅宗的影子。应该说,“禅宗文化”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早就潜在了。
近现代有不少的学者认为,禅宗能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渗透力,主要因为其没有像唯识宗、天台宗等那么多的理论求证与修学阶位。禅宗删繁就简,一念开悟即可横超生死海,直入如来地。这是就禅宗的教法与教仪特色而论的,诚然不失为有识之见。东晋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较深的认识,他也讲过:“秦人尚简”。
然而,透过禅宗这种简捷明快的“表相”,我们是否看到其内在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追求人格平等的思想意识及其独特的艺术气质。
在记录慧能一生教化言论的《坛经》中,显著地存在着人格平等的意识:“下下人有上上智”。这直接向儒家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论调提出了挑战。慧能敢于冲破上尊上智下卑下愚的思想牢笼,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先进的人文理念,为禅宗学说的演进奠定了基础。
慧能独特新颖的说教,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改变时尚的禅师。据载在其座下得法者甚众,被印可的弟子遍及大江南北,各布化一方。至中唐时期,禅宗的新教义已形成了成熟的思想体系,天下各大丛林各具风采,造成了鸢飞鱼跃的学术研究大格局。
由慧能发起的禅宗改革,不啻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它波澜壮阔,回响久远。曹溪第6代的临济宗开创者义玄倡言要做“无依道人”,意思是要众人自立,不做倚傍圣贤的奴才。要敢于“弧明历历地”出入三界,并且“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饿鬼说饿鬼。向一切处游履国土,教化众生……”(《临济录》)。他常苦苦提撕学人:“且要自信,莫向觅。”(同上)又告诉求法者:“有一般学人向五台山里求文殊,早错了也。五台山无文殊。你欲识文殊么?只你目前用处始终不异,处处不疑,此个是活文殊。”(同上)禅宗极力主张“自信”的理念,正是争取人格平等的哲学基础。
禅学要求学者以形象思维去理解玄妙的哲理:“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大珠禅师语录》)。用妙悟去参透难以言诠的体验:“空门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滋味长。心地不生闲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古尊宿语录·法演和尚语录》)大凡读过“灯录”、“语录”一类禅书的人,都莫不被其中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精彩的艺术语言所感动与倾倒。这类记言体式的典籍,以 载录禅师开示学人的“法语”为主要内容,当中存有大量的诗偈,因为禅师们总喜欢以诗代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禅宗的历史就是一部诗史。历史上不少“诗僧”在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瞩目。禅宗还以其宽博的襟怀迎纳为数众多的文人居士加入到“禅诗”的创作行列中去。如前面提到的王维等著名诗人学者,无一不是禅诗创作的积极分子。禅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禅宗流衍到宋代,几乎“诗化”了,而恰好在此时期,诗歌的批评出现了高潮,“诗话“特别繁兴。《沧浪诗话》的问世,标志着诗歌创作的理论研究步入自觉的阶段。该书的作者严羽在开篇之始的《诗辩》中明确提出“论诗如论禅”的主张,并认为“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的观点表明:中国传统诗学不但早已接受,并且把禅学中的某些重要理念作为诗歌创作的指导理论而将其确立起来。这是中国诗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禅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它不但在诗歌研创方面取得显赫成就,放射出无法抗拒的魅力。同时,在书法、绘画、茶艺等诸领域也影响深远,产生了所谓的“禅书”、“禅画”与“禅茶”。
深入探求禅宗文化中潜藏的倡导人格平等的哲学意识与张扬生命个性的艺术气质,拟应成为我们研究禅宗文化的时代任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禅学之所以能根深蒂固地长存于中国文化土壤里,原因是它弥补了儒家学说所欠缺的平等文化与个性文化。
对于参究禅学者而言,其要妙体现在能否感悟到“无碍”的境界。学者本着人格平等的意识(哲学理念),通过活泼的妙悟(艺术意趣),进出人我平等、万类自适的境界,这就是禅境。苏轼有诗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这是诗人游访庐山并应东林寺长老之请留住一夜后所创作的。诗人把珍贵的灵性与圆深的禅理赋予无限自由的水声山色。可以窥见:诗人当下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生机而又恬静的世界。正是置身于如此美妙的时空里,诗人表示:自己在一宿之中悟到了无穷的生命意义,但却难以向他人道。解读苏轼这篇上乘之作,相信会加深我们对禅宗文化的哲学与艺术底蕴的体悟。
二OO四年五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