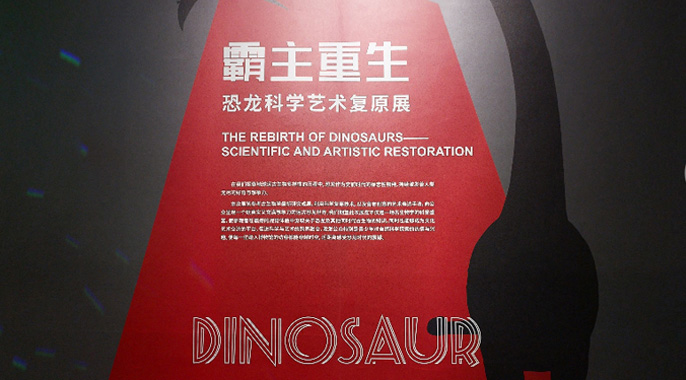创造者的元年
从过去剩下来的只是人们从当下的角度能够建构起来的东西。
——莫里斯·哈布瓦赫《记忆的社会框架》
艺术史上的每一次觉醒,都是创造者对混沌的凝视与重构。本次展览《创造者的元年:李山与宋徽宗》,将两位跨越千年的艺术家——当代艺术先驱李山老师与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并置对话,试图展现在神话与科学、记忆与遗忘的裂隙中,艺术本体如何以创造者的姿态,留下人类对生命与永恒的认知。当李山以画笔从苏美尔的神话中叩问生命的本源,当宋徽宗以瘦金体为“仙卿”的龙章云篆题字,他们皆以艺术之名为时代镌刻下一道“元年”的刻痕——这刻痕并非纪年的符号,而更像文明基因中永不褪色的遗传序列。
李山,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其多元的艺术实践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影响了中国乃至全球的艺术界。他在长达5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不断探索生命的本质和生物艺术的边界。他的作品从早期的《扩延》和《秩序》系列,到90年代的《胭脂》系列,再到近30年的生物艺术创作,展现了其对生命神秘性和生物性的持续关注。近年的系列《苏美尔的徊响》是一道向远古神话投去的当代目光。这位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驱者,无论是抽象的形式,还是生物艺术的尝试,一直在思考着生命的起源,如今我们跟随他从实验室的试管返回先民的陶罐,将基因编辑转化为一场艺术的降神仪式。画布之上,苏美尔神话中的创世“大神”阿努纳奇们与早期人类命运缠绕共生,就像忧郁的蓝与妖娆的暗银交织成的笔触,暗示着争斗如何被编码进文明的底层逻辑。这种对生命本质的干预,既非科学的附庸,亦非审美的玩物,而是从艺术的角度对“创造者”身份的终极诘问:若神话中的神祇曾将争斗的种子植入人类基因,今日的艺术家能否以画笔,为文明嫁接一株新的可能?
李山老师选择的对话对象是宋徽宗,在《苏美尔的徊响》背面,即宋徽宗的《龙章云篆诗文碑》拓本,记录了宣和元年的一段神秘事件:政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黄昏时,仙人降临凡间于坤宁殿,并留下了“云篆”墨迹。碑文之上,“仙卿”的云篆如飞鸟掠空,瘦金体的题记则似寒刃剖玉,在自由与法度的临界点上,凝固了一场人与天地的密谈。宋徽宗以帝王之尊,却甘为艺术的僭越者:他打破书法的藏锋传统,以尖峭的线条刺破纸张的沉默,将瞬间的神启转化为永恒的秩序。若说李山的创作是对生命密码的“解码”,宋徽宗则是在书写宇宙的“源代码”——实验室与祭坛已不分古今,在艺术的维度上殊途同归:创造的本质,乃是以有限之形,捕捉无限之力。
如果静心观看,观者或许会发现展览的唯二两件作品都有着一种特殊气质,宛如昆体良所谓的“高大而古老的橡树,让人肃然起敬。”那是一种高贵灵魂的回声,这种回声或许恰恰为当代艺术所需,仿佛一位来自“健康时代”的原始野蛮人镌金凿石、纪烈荣神,闯进在“衰败时代”中淫巧侈丽的宫殿里拔剑四顾。这种力的流转,恰如文明记忆的螺旋。杨·阿斯曼曾言,记忆需借文字、符号与仪式,方能超越个体生命的桎梏。苏美尔人将历史视为诸神意志的显影,以泥板铭刻战争与祭祀;宋徽宗以云篆碑文将仙谕凝为文化基因;李山则以生物艺术将基因的创造升华为当代神话——三者皆在完成同一使命:将混沌的经验锻造成可传承的符号。贡布里希在《偏爱原始性》中慨叹“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丢失,这些丢失只能在后来的岁月逐渐恢复。”而艺术家正是那些在丢失的暗河中打捞光斑的潜泳者。李山画中大神的暴烈、神圣与暧昧与宋徽宗笔下的瘦金体,皆是对“原始性”的再诠释:前者以想象与艺术直觉模拟生命的野性,后者以法度的庄严收束天意的无常。这种螺旋式的上升,不是复古的怀旧,而是将远古的基因注入当代的躯体,令文明在变异中重生。
这次展览也是一场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对话,科学思想常常处在违背直觉的抽象世界之中,不是人的感官所能经验的,它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沉入到心灵的底层,成为共同信仰与态度。普通的经验对象或场景在自然科学中常常被剥去个体的独一无二,在科学的表述范围中,世界的直接特征因归约而失去。但艺术在其中起作用的直接经验的世界仍保持原来的样子。自然科学并不预示着诗歌即将死亡,这是因为,人越是接近于自然界,就越是清楚他的冲动与想法是由他的内在自然作用的结果。人性在其重大运作中,总是按照这一原则行事。科学给予这一行动以智力支持。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感受,总是以某种形式成为对艺术起触发作用的精神。
今日的科技时代,记忆正被技术解构为可复制的数据,仪式的神圣性消散于屏幕的碎片中。当人工智能试图将一切归约为算法,艺术的使命愈发清晰——它必须成为那个“不可归约的例外”。李山的基因绘画中,生命原初甚至异样的形态是对标准化生产的嘲讽;宋徽宗的云篆碑文上,每一笔锋的震颤都是对机械复制的抵抗。他们的作品提醒我们:真正的记忆从不存储于云端,而是镌刻在基因的碱基对间、凝结于笔尖的墨痕深处。范景中先生曾在《艺术与文明》中说:“宇宙间或许有更高级的生命,但未必有更高级的艺术。”当李山以《苏美尔的徊响》展开基因的双螺旋始祖,当宋徽宗以瘦金体勾连天地,他们不仅在定义艺术的元年,更在文明的基因库中埋下一颗颗等待觉醒的种子。
“创造者的元年”从未终结。它活在实验室荧光下的细胞分裂中,活在宣和元年石碑的风化纹路里,活在每一位观者凝视画布时瞳孔的震颤中。展览中的两件作品,恰似文明长河的两道支流:一条从未来的实验室回溯远古,以基因的序列质问生命的可能;一条从远古的碑刻流淌至今,以书法铭刻宇宙的秩序。而它们的交汇处,正是艺术永恒的起点——在那里,创造者以勇气劈开混沌,为人类写下另一个纪元存在的可能。
陈研
2025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