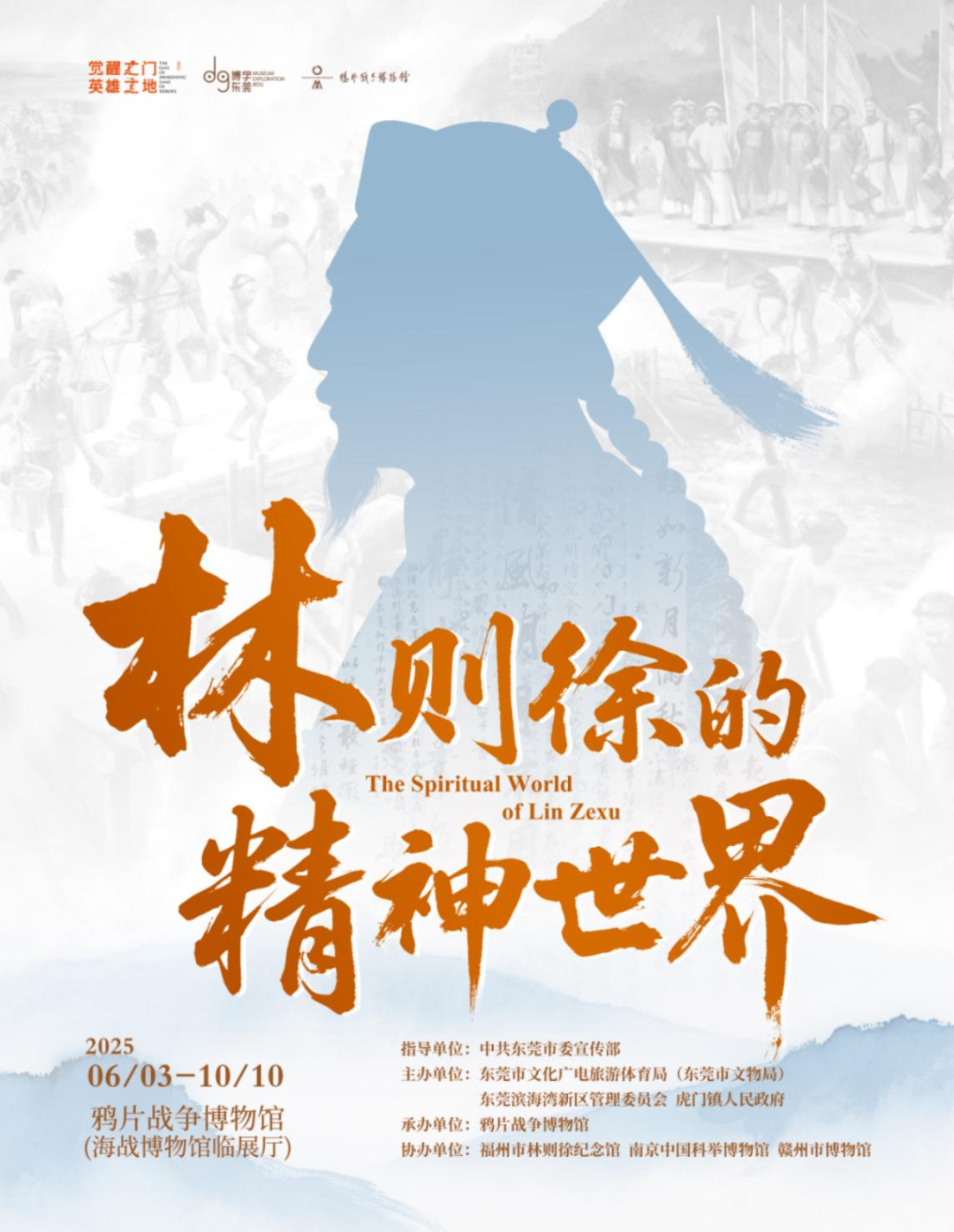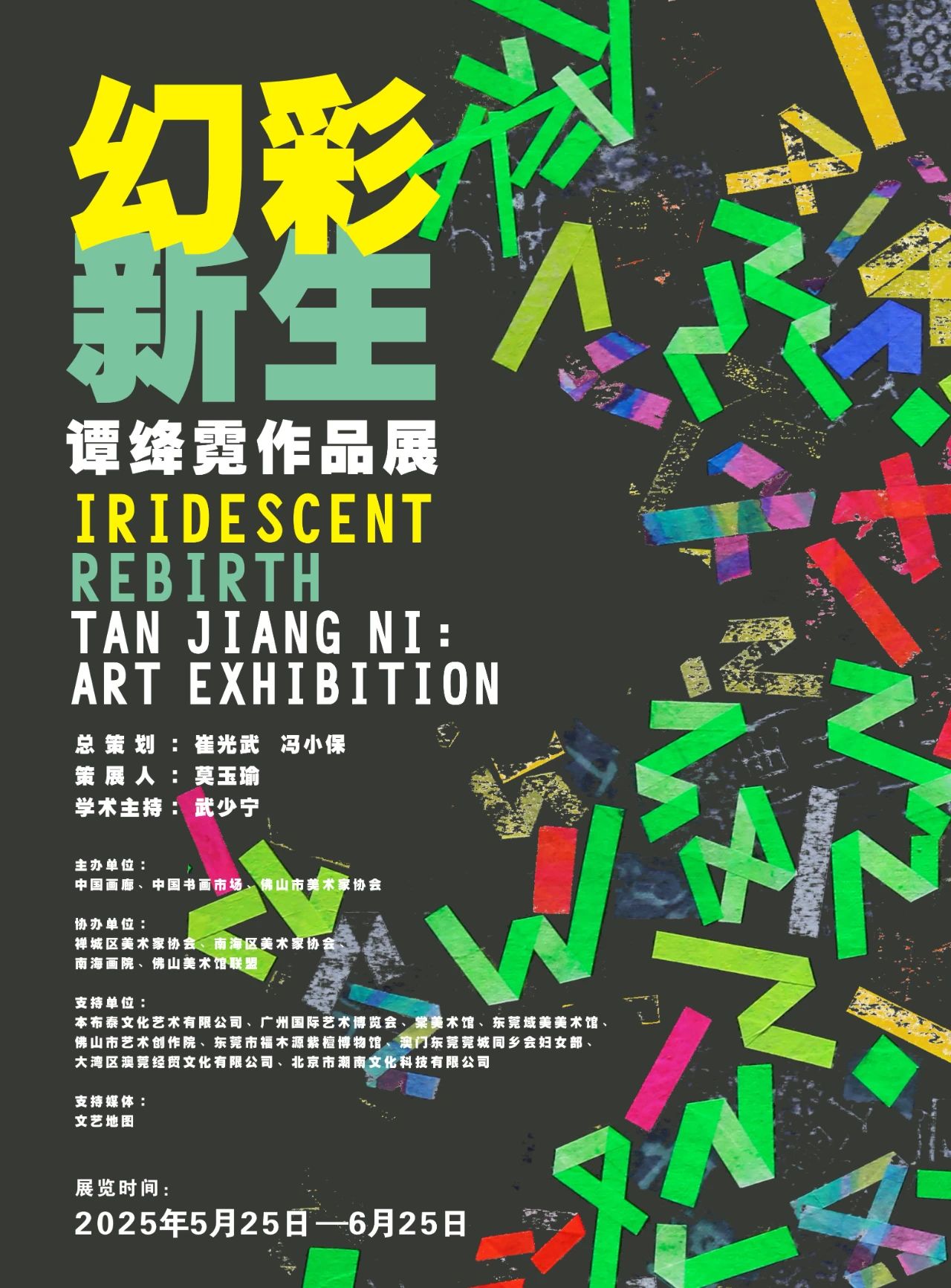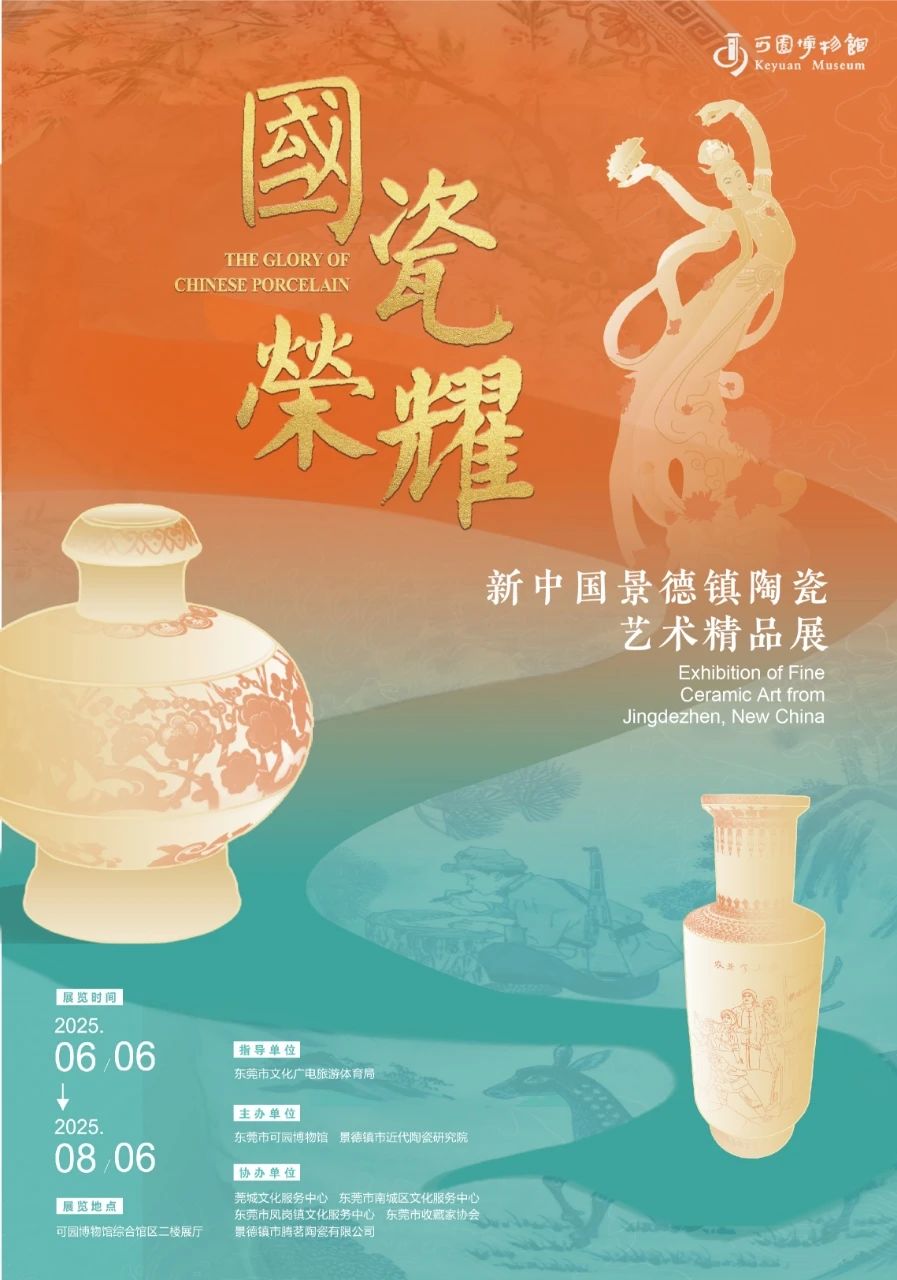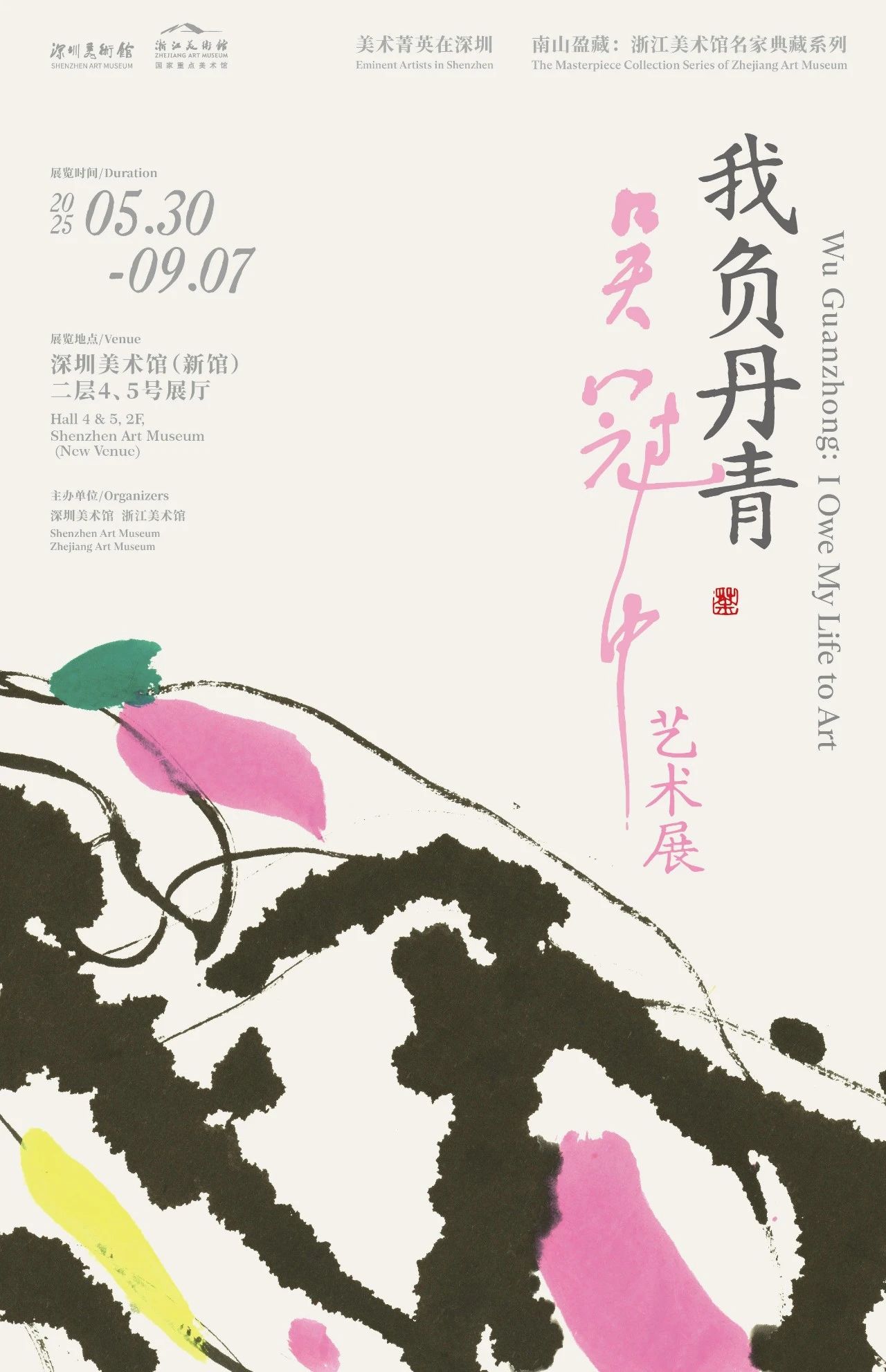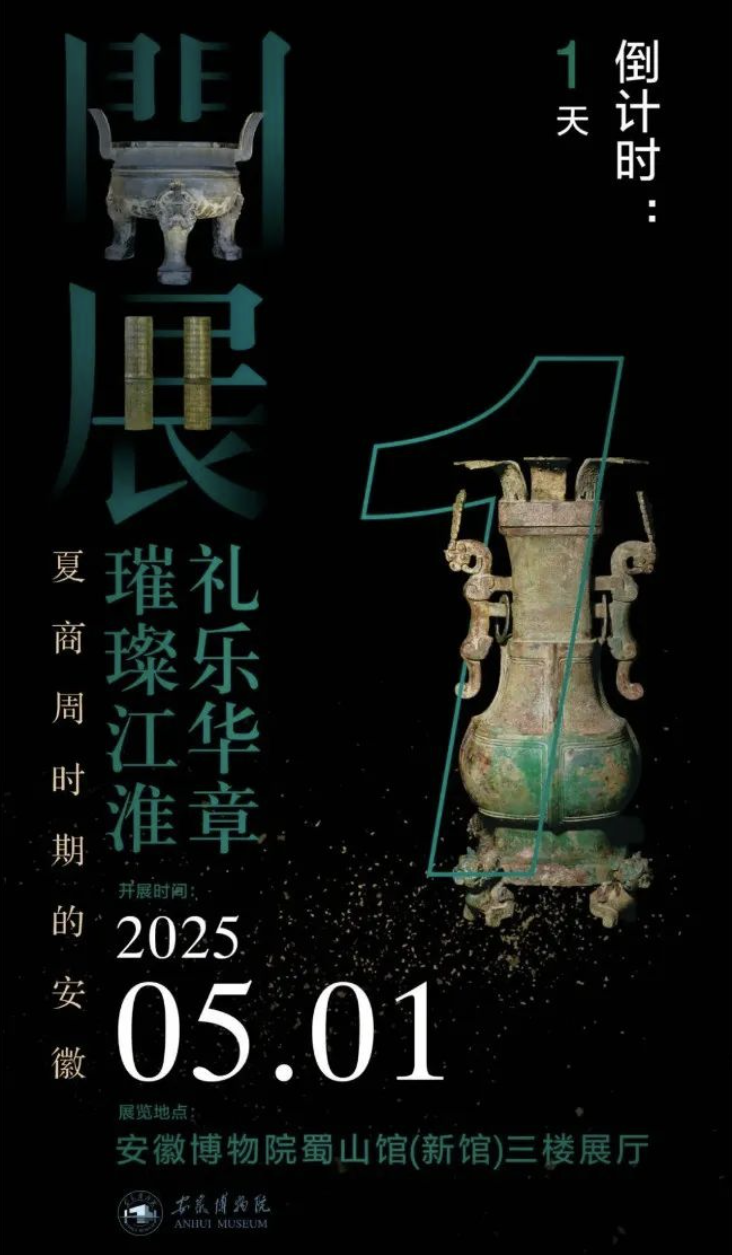菲利普·K·迪克在其1969年出版的小说《尤比克》(UBIK)提出一组设定:在科技高度发达的1992年,人类可以将意识转移到储存容器之中,同时冷冻肉身,这样即便身体死去,意识仍然可以存在,从而进入一种半生半死(half-life)的状态,沉浸在一类类似于“虚拟现实”的内在体验中。但这种“虚拟现实”又有别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由高技术手段所生成的世界,这是一个由技术、意识、记忆和感知交织而成的多层次的扭曲现实,随着每一次“半生半死”的人尝试与他者进行沟通的时刻,逐渐塌缩——时间流转、物体变化,甚至连自身的存在也开始动摇,时间、空间及真实的物理法则都不再稳定。
应对这种塌缩的是一类名为“尤比克”的神秘物质。在故事中,这个麦高芬(MacGuffin)可以以各种日常商品的形式而存在,如胶囊、喷雾剂、洗发水和巧克力等等。处在“半生半死”状态的人,能够借助尤比克来恢复感知的清晰度,从而分辨现实和虚幻,对环境的扭曲做出抵御,以此缓和肉身之死所带来的秩序解体。
本次祝金坤的个人展览,其灵感来自于上述《尤比克》的设定所带来的联想:小说中由技术支持、又为主体情感所牵制的中阴地带,也是我们此刻面对技术环境的身心写照。人类对于时间、记忆、空间、自我意识以及死亡的感觉,都被卷入这个由技术所构成的外部环境之中,换而言之,被抛入(thrown into)了数字化生存的处境。是故,对于一个存在者而言,他能够进入这个世界的唯一入口,就是他在媒介之间找到的位置(档案化的社会身份、作为数字资产的个人数据、网络世界的虚拟人格、电子游戏中的角色扮演……)。治理技术下的特定操纵、非真实的图像、难以识别的真伪信息,这些外在性因素构成了所谓的“超真实”情境,同时缠绕着发自主体内部深处的欲望、情念和记忆等因素,令外部环境和内在的心理现实都不受主体意志所控地发生形变。上述因素的共同存在,在构成人之主体的同时,也瓦解了主体性的神话。而这种生存构想,既以人类为中心,也破坏了其自身的稳定性——既让主体构成,又让主体裂解——恰如非生非死之态,又随着时间之流的运转而趋向于“熵”的状态。
在本次展览之中,祝金坤给一个随着死亡发生而开始崩塌的时刻按下暂停键,尽管这个瞬间仍被低面模型的图像包围,但实存之物又从其中绽出和凸显。空间中的药丸本是来自电子游戏中红蓝药水,自身也作为一种避免角色死亡或魔法耗尽的道具而存在,一如“尤比克”这类神秘物质,给技术时代的幸存更多的肯定性。因而人与这个被称作后真相时代的现实之关系,似乎稍稍地被赋予了更多实感。所以,不必那么悲观。就像阿曼达·拉格奎斯特(Amanda Lagerkvist)曾经给出的提示:在死亡、丧失、冲突、苦难等极限境遇之时,为生命负责并赋予其形式的责任就会自动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