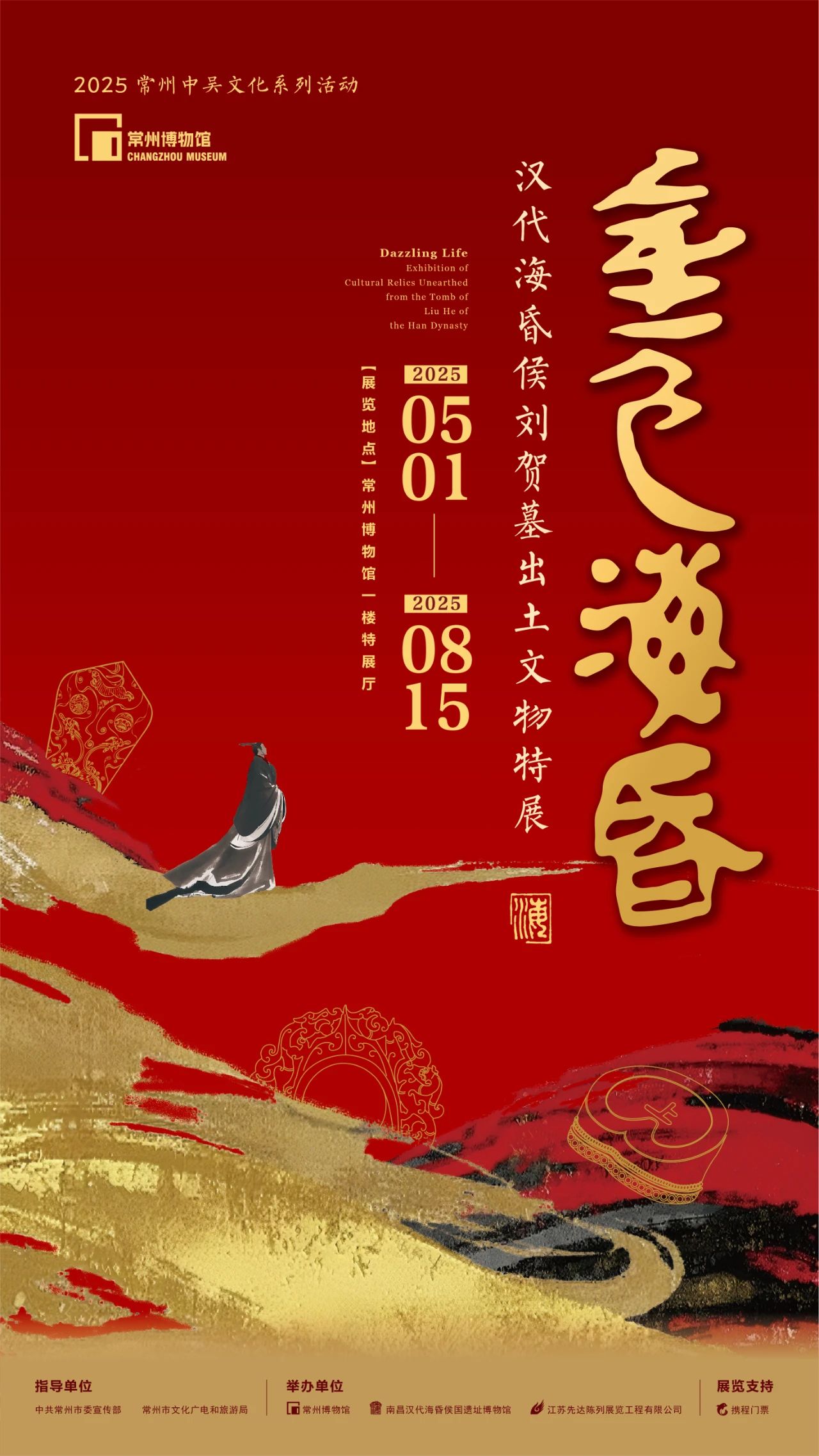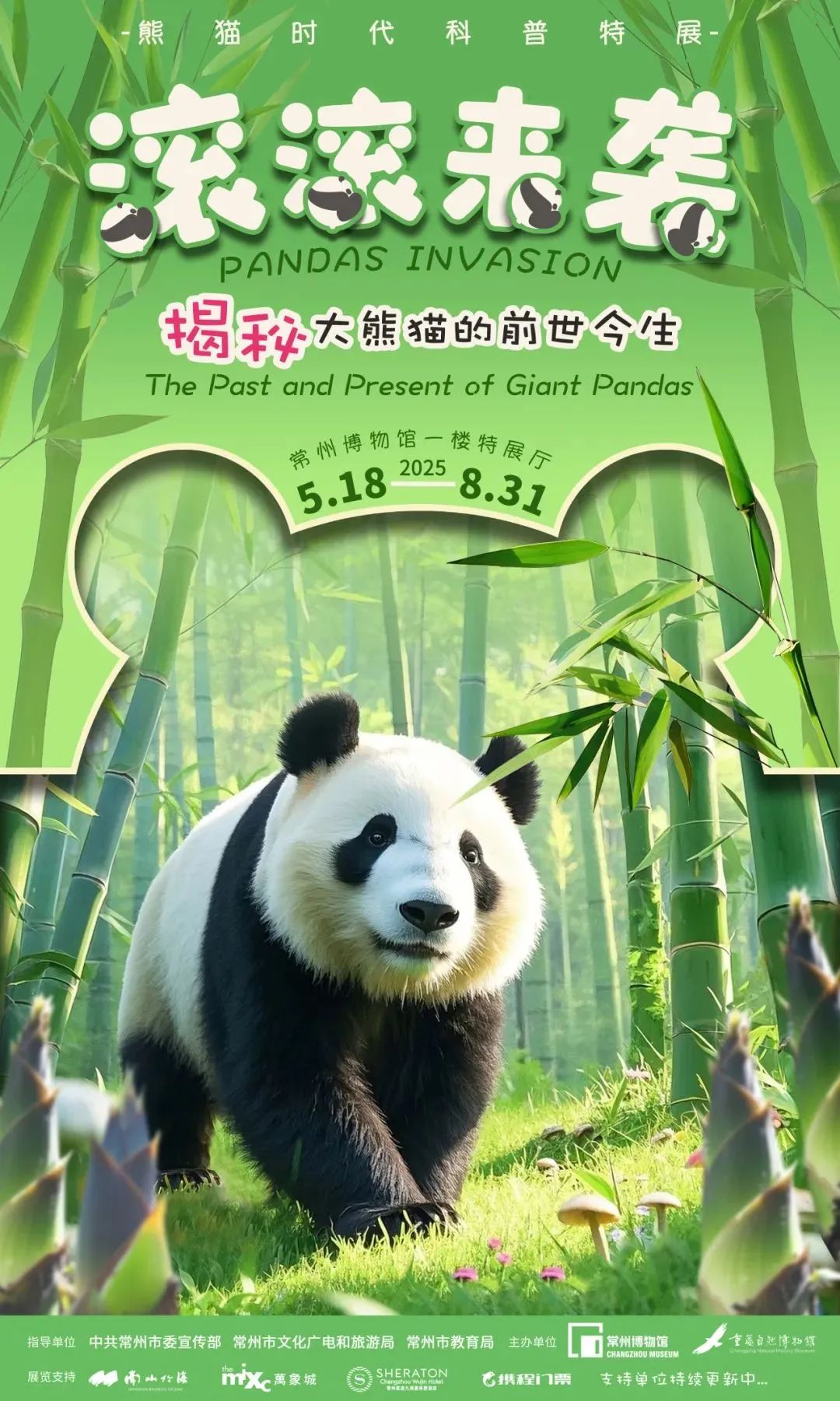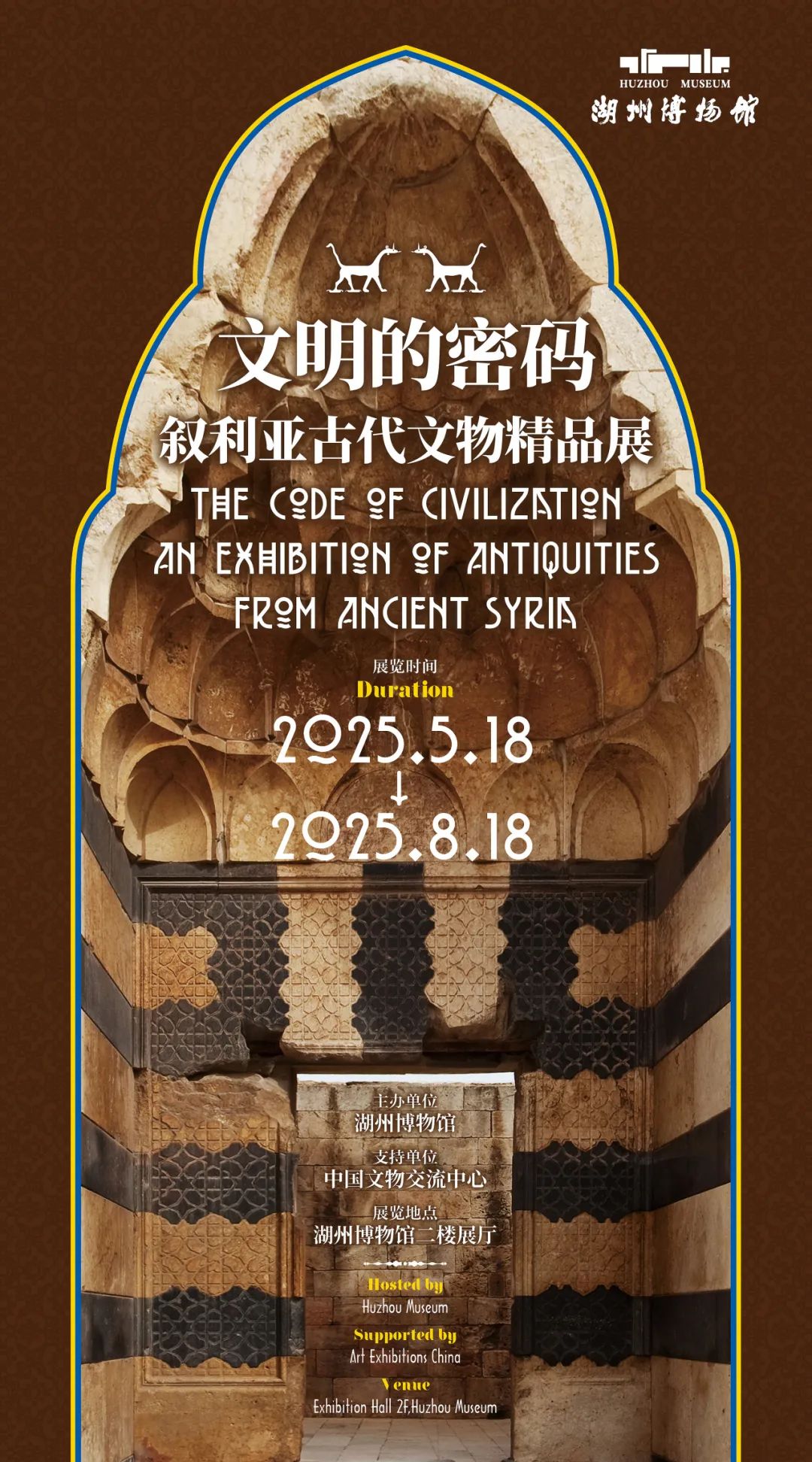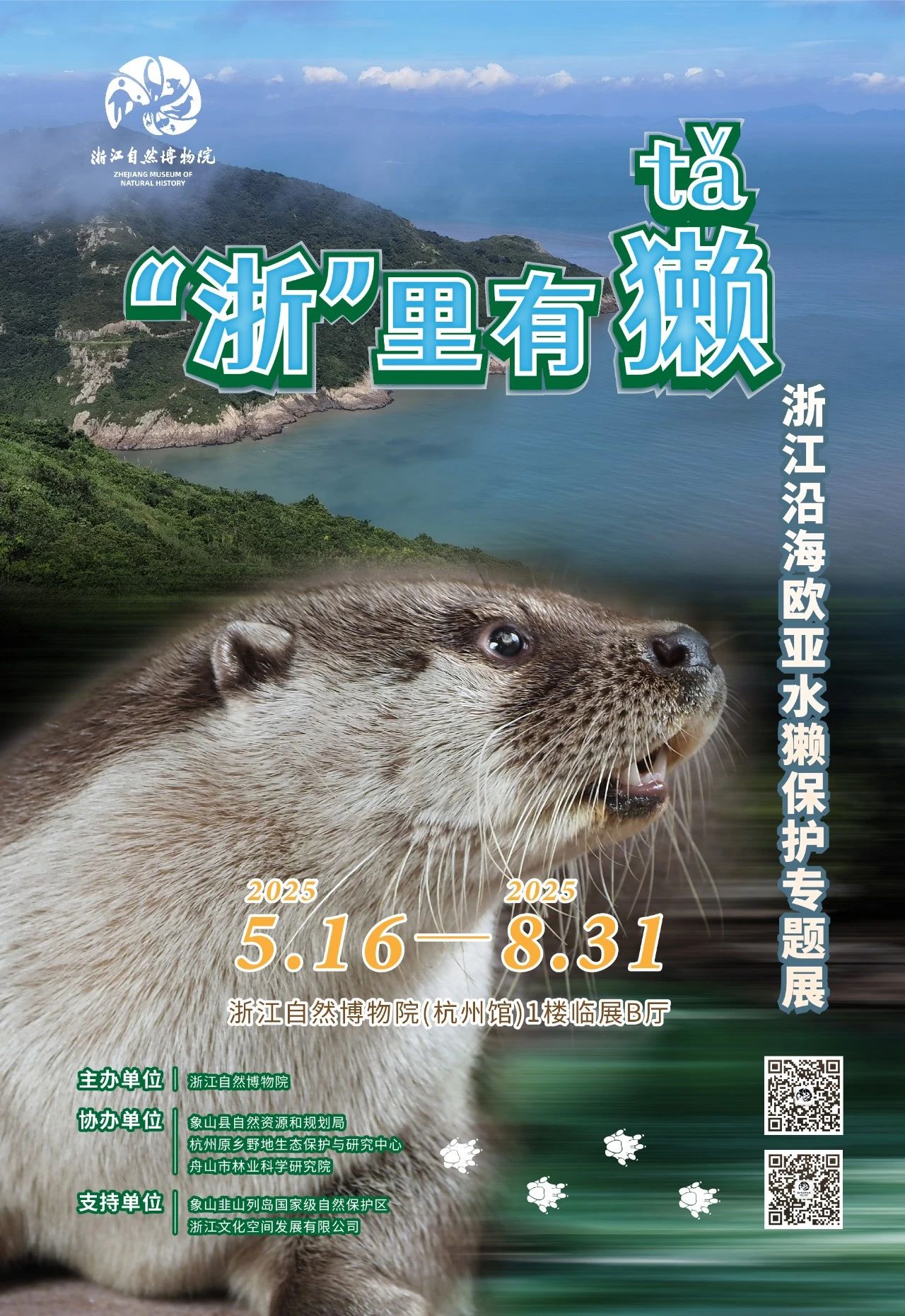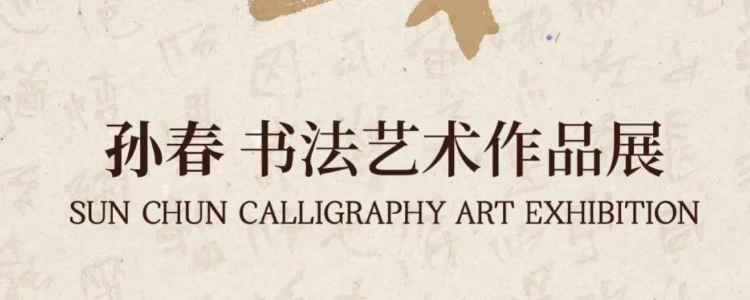
首先,孙春不是职业书法家。在所有把某种行业当作职业的人眼中,立场基本是预先设定的,这是关系饭碗的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很少有人会做出砸自己饭碗的事(也不是绝对的)。所以,选择职业书法家作为判断书法未来的样本,结论不具有说服力。
第二个原因其实是我前面说的,孙春的书法方式,无论是他长期临帖形成的,还是就是他本人的一种刻意选择,因其书写方式本身所产生的形式上的趣味性,提供了一种跨越文化语境的比较和观察可能。而这一点,有时对于思考某种文化类型或是文化成果的未来形态,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不是说,要把孙春的书法拿去和中国书法之外的一种书写方式进行硬性的比较——中国书法的独特性也使我们在今天很难找到这样的目标——而是说,他的书法和人类最古老文字的直观相似性,让我们可以尝试在一个更大跨度的时间范围和文化圈层进行考古,避免我们在中国书法内部长期兜圈子产生的视域狭窄的麻烦。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文字的产生是历史的过程,它也必将流变乃至消亡。书写的方式就更是这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未来的社会,没有单纯的艺术家,只有把艺术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换句话说,一种艺术形式的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只有更多人的参与,并且是非职业化的参与,才能成为可能。中国书法具备这种可能性。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谈了艺术和艺术的未来,但我们不难从中领会到,马克思其实也从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为艺术和艺术家指明了未来的道路。
很庆幸,孙春正站在这条大路的路口,这也是他进入我们观察视野的原因。孙春虽然自幼习书,且长期笔耕不辍,但他也是穿白衬衫的警官。所以,他的书写行为天然地剥离掉了书法的职业化外衣。
历史的看,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字是人类智慧和情感的外化手段,书写和纸张是承载这种手段的工具。在人类文明史上,智慧外化的作用不言而喻。也因为这样,让我们忽略了情感外化的比重。实际上,中国书法发展到今天,作为智慧外化的工具性早就已经不复存在,当然,作为职业的价值可能性,或许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果有,旧社会衙门口的代书者或许算是一种)。但书法今天仍然能够深受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喜爱,这其中的原因不在于其工具价值,而在于其情感价值。仓颉造字而鬼神哭,或许不完全是出于鬼神对人有了智慧的担忧,可能也还有他们对人找到了情感寄托之物的感动。
情感外化的坚持,为中国书法提供了从工具价值上升到情感价值的可能。颠张狂素的颠和狂不正是情感的表达?作为工具价值的书法与作为情感表达手段的书写,显然面貌是不一样的。前者强调的是外在的规则,后者强调的内在的自我。孙春的书法每一笔都像戳到了五、六千年前的泥板上,显然他不太在意文字外在的具体意思,更在意于让笔墨和纸张的经营去承载他个人的某种内在情绪。用今天流行的话说,书法为他的生活提供了某种“情绪价值”。
巴别塔之后,语言和文字就成了人类文明的藩篱,这是我们审读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最大的障碍,或许也是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最本质的原因。我这里不是说孙春的书法突破了文明的藩篱,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可以展开丰富想象的图景。就像马丁•路德•金说的“我有一个梦想”,它感动了所有人。梦想的背后是人类的情感,毕竟,我们承认,人类的情感相通的。从这个角度说,汉谟拉比法典、罗塞塔石碑、兰亭序、爨宝子、铁山摩崖,甚至是江永的女书,他们所传承的,何尝不是一种情感。
在今天的大部分人看来,博物馆中的过去文字我们并不能认识很多,那些法典和文书,也早就失去了实际的价值,但我们都知道,它们很有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历史和文化的,更是一种情感上的,这种情感上的价值具有最普遍的可读性。我想,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第一次见到孙春的书法,就会有一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原因。他的作品中传达出来的不是那种抄书匠般的工具价值,而是一种认知和感觉上的情绪。
对于如何观照当代语境下的书写,克莱夫•贝尔曾经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有趣概念——有意味的形式。或许,被剥离了功利属性和工具价值的书法,作为艺术的重要门类,也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在这样的概念下,反倒获得一种可以一直传承下去的可能性。
——2024年10月1日写于黄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