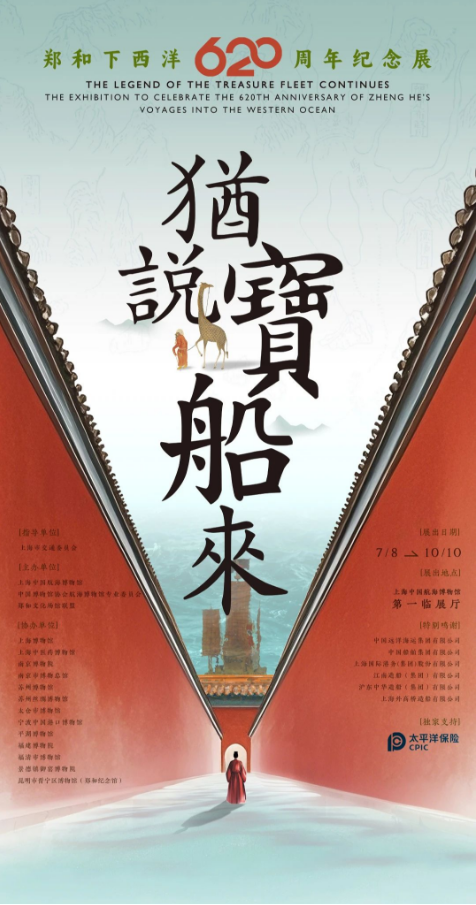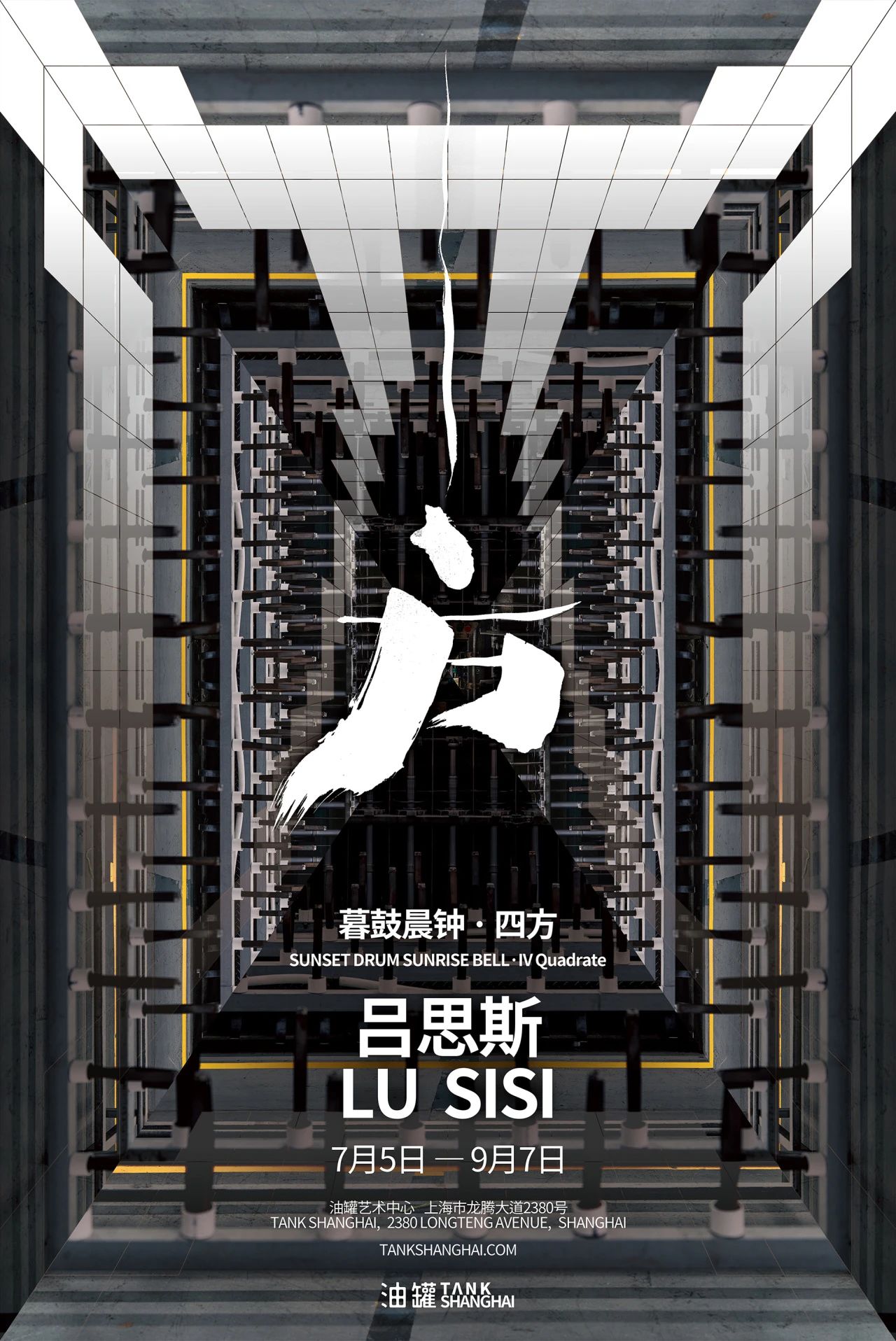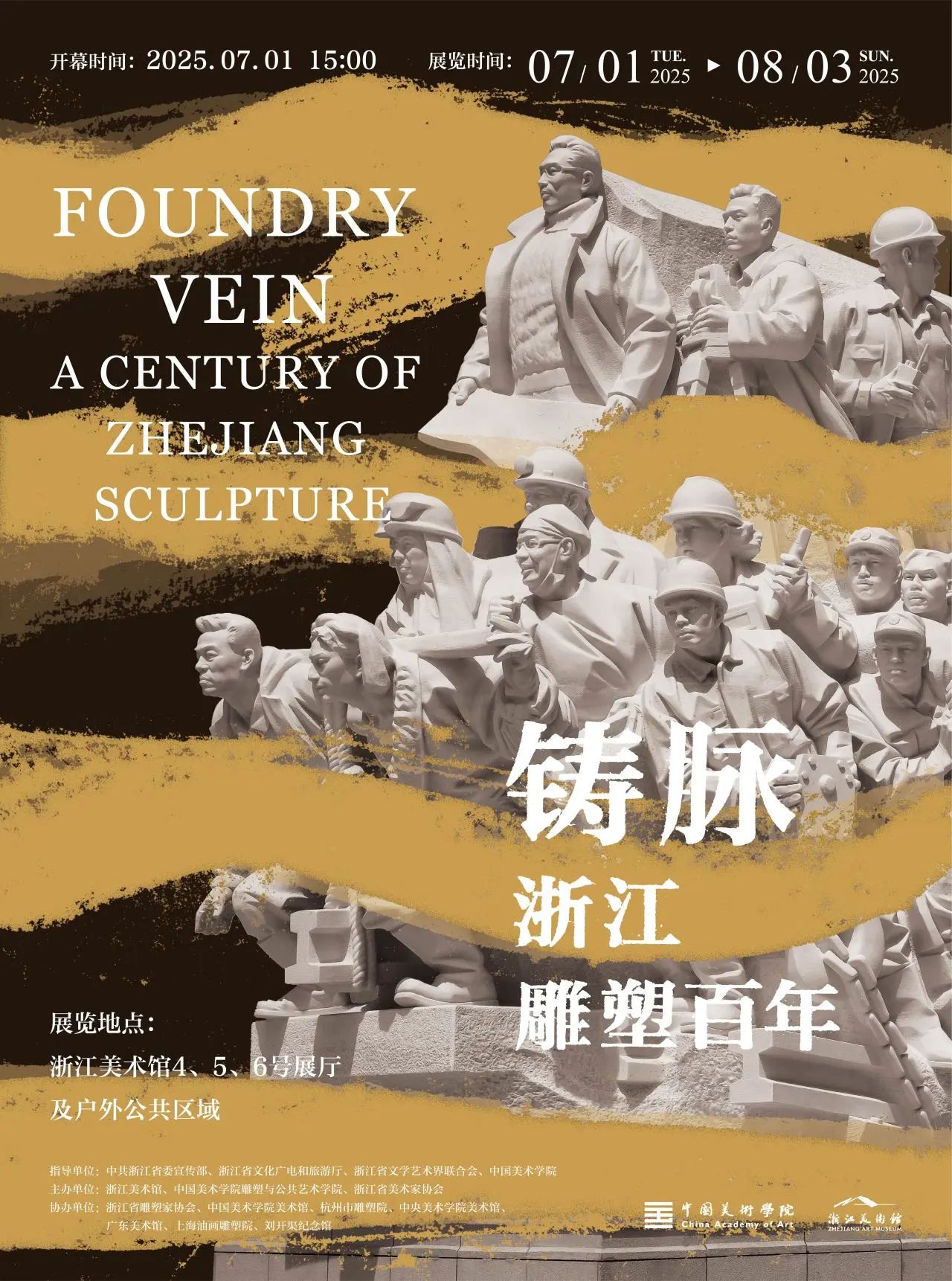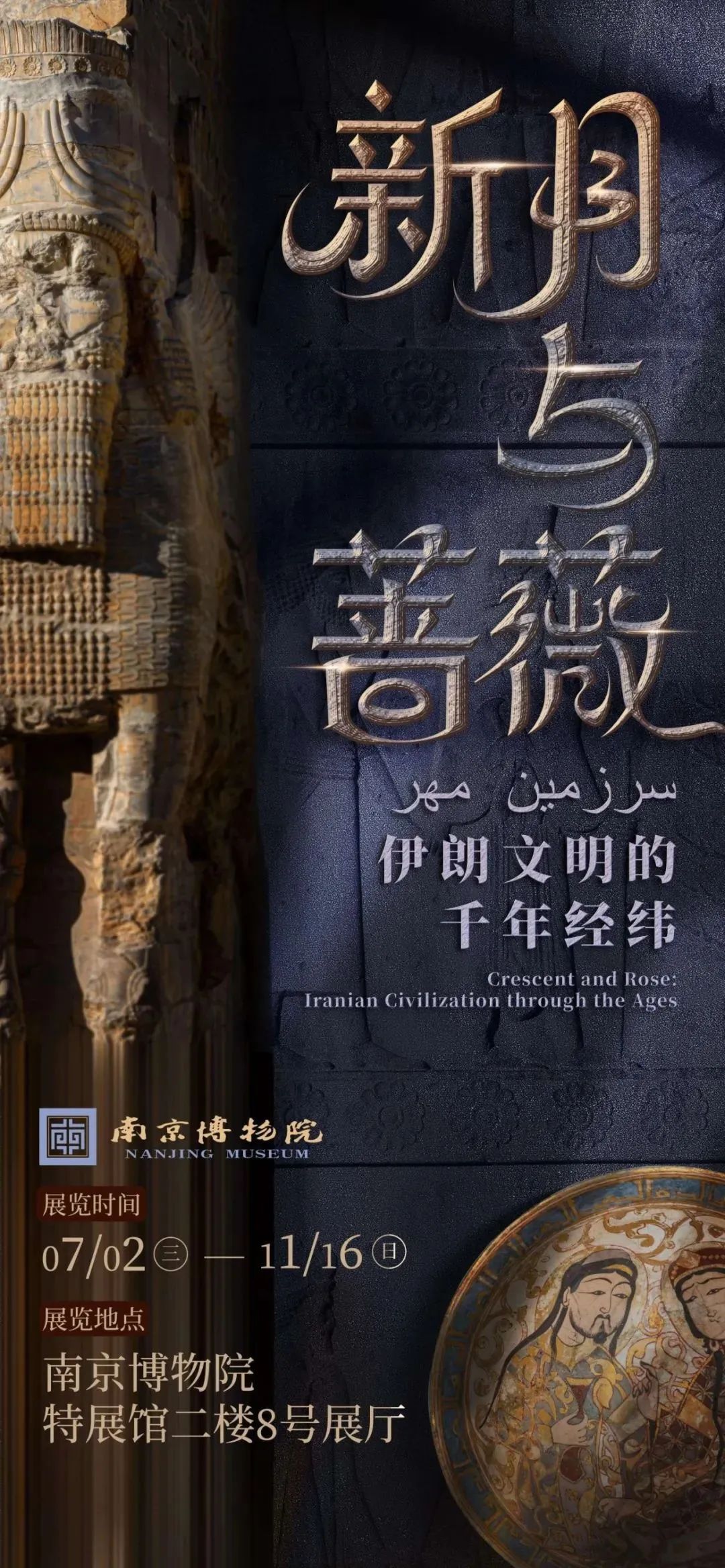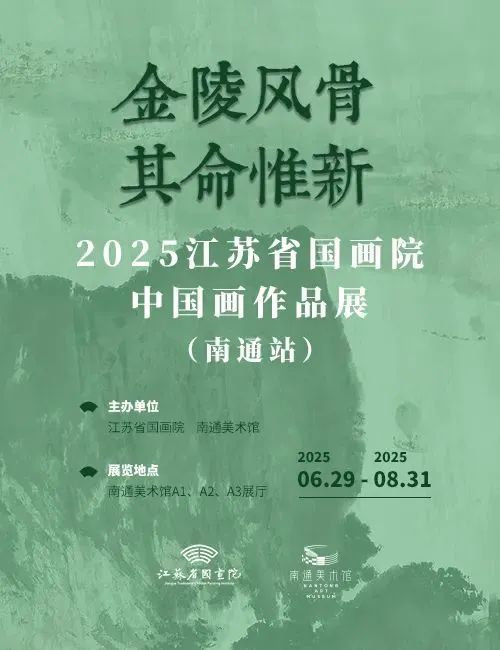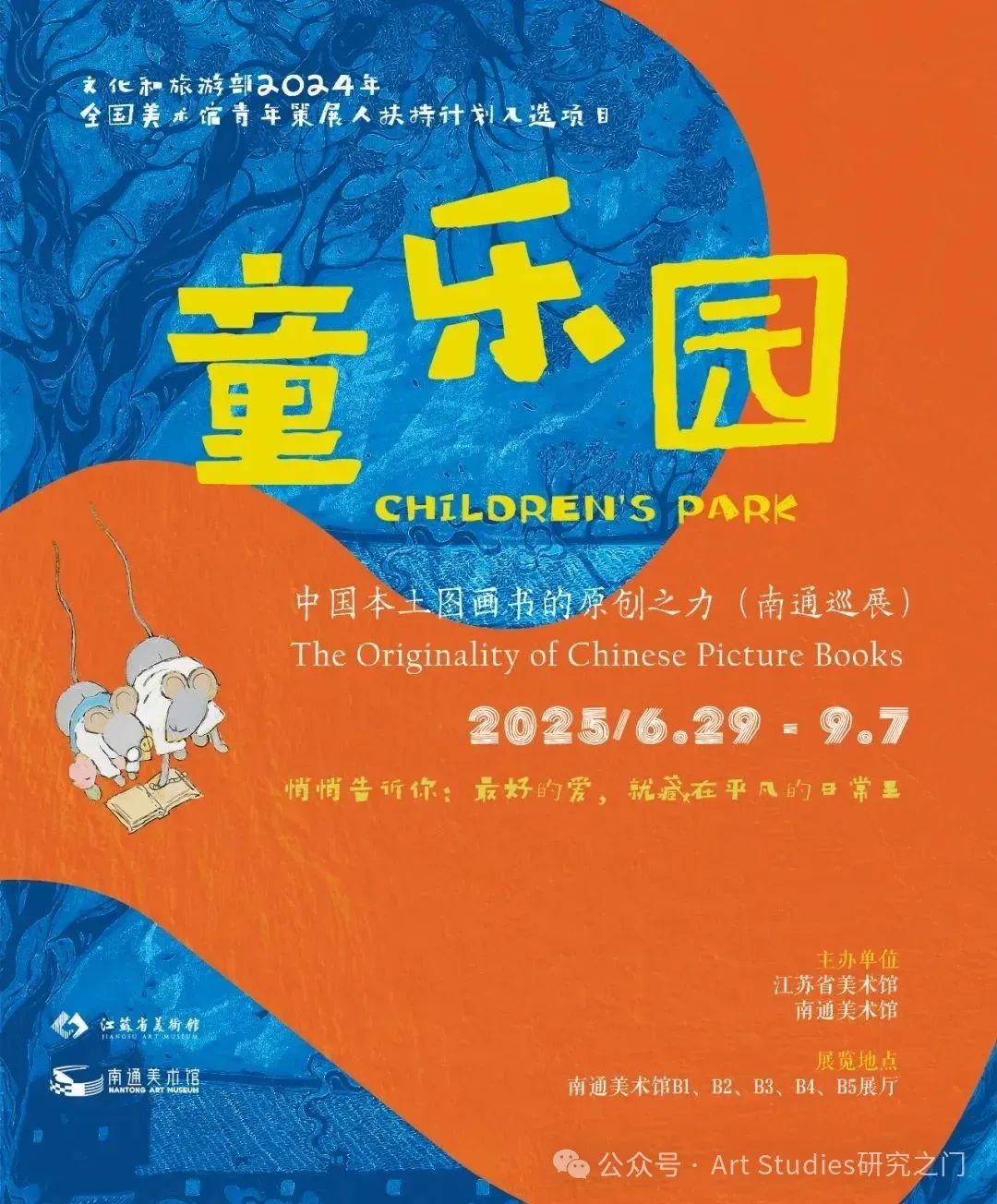我是衲子,今年八十五岁了,画了不少年的画,遇到了不少明师益友,给予我很大帮助。现在,我把这些讲出来,一为纪念他们,二于后来者而言,也有启发之用吧。
启蒙岁月
由于在京的祖父是擅长骨科的中医,我的幼年时期,一直生活在传统医学的氛围里。祖父是个很有威严的人,他曾想让我继承家学,少年时期一度要我在家学中医,不许出门。后来, 姑父提议先让我去外面学针灸,祖父同意后,才把我放出来。结果针灸还未学完,我就大病一场,自此没再坚持。
那时候,家中有不少匾额,有的挂在屋里,放不下的就挂在屋外。记得部分匾额用墨书写,其中一幅是清末书法家金梁(金息侯)的“炼石补天”,那遒劲的笔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凭着兴趣,开始尝试在红模本上描摹写画。这些匾额伴随时代的变迁消失不见,再次看到,已经被家人当成案板了。
1953年,我随家人回到河北老家,过了几年乡村生活,收获了一段安闲、平静的时光。
记忆里,乡间农忙之余,人们一有闲情,便以相约写书法为雅趣,以背写书法高手字迹为荣耀。聚在一起评“书”论“道”,成了一桩乐事。此风尚曾染及十里八乡,只要相传有书写或点画可以观摩者,大家都会来看个究竟。我对书法的兴趣,由此渐至浓厚。
后来每次回老家,都有乡亲和书法爱好者来切磋书法,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在乡间我也见过几位很有功力的老先生的作品,因条件所限,未能把他们的作品保存一二,实在遗憾。
1955年,我返京读书,途中见到很多旧书摊上有碑帖售卖,多是颜、柳、欧、赵诸体,没承想何绍基的书法已成为我最喜品赏的字迹。1955年至1958年,我在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就读,这期间开始真正进入花鸟画、书法的学习阶段。
拜师张慧中先生
1956年,经家里一位董姓师伯的介绍,我去拜访王雪涛先生,意欲投先生门下学习花鸟画。为了让我打牢功底,雪涛先生教我先在张慧中先生门下学习兰竹、兼学书法。自此,我结束了颜、柳、欧、赵的习字启蒙,正式进入花鸟画、书法的学 习阶段。
印象中,张先生的个子不是很高,四五十岁的样子,外形秀气,性情温和。她住在西城绒线胡同,离我住的石碑胡同不远,家里有个院子,除了她和丈夫,同住的还有她的侄女。我见过她侄女的钢笔书法,朴拙有力,应该得到了张先生的点拨。我受张先生的教导,有一年的时间。
张先生看我用笔虽未得法,但还算沉着,决定先授我篆法执笔法。之前,我对此笔法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感到十分新鲜,后历经多年,一直沿用此法。
初学此笔法,需指实掌虚,虎口如龙眼,腕肘皆悬,只作横竖两画,以练习笔画,排满九个大方格。在写篆书之前,我描红模子、临碑帖已有几年,因为那会儿的学识不够,而篆书需要认字,过了相当时日才做偏旁部首练习,又过了相当时日 才写整字。写篆书时,张先生曾推荐我看《泰山刻石》。她说过,篆书的笔画写好后,中间是一道黑线或者一道白线,从头到尾,这个用笔就算是好一些的了。
张先生还曾示范魏碑(郑道昭)的写法以及《天发神谶碑》的用笔,只觉锋芒过处,似有千斤之力。
学画兰竹,也是如此。兰叶、花、茎,竹干、枝、叶、节像作字那般先分步骤练习,而后才是水墨、墨彩的尝试及至掌握。每日洗砚磨墨,到课结束、洗笔十分洁净后, 还需妥善放置。经过此番,至今仍觉得有一种修禅的意味。
多年后,我也养成这样一种工作秩序,师承张先生的笔法并养成执笔高提管的习惯。后来,我看到了徐渭的《论执管法》,正合前学。
参加“业余进修班”
1958年,《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中国画院(现北京画院)“业余进修班”的招生信息,进修班分山水、花鸟、人物三个专业,当时我十八岁,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花鸟专业的学员。三个班一共招收了六十人,其中花鸟专业又分工笔花鸟和写意花鸟两个班,工笔花鸟由于非闇主讲、俞致贞辅导,写意花鸟由王雪涛、汪慎生主讲,娄师白辅导。两个班有共同课,崔子范、陈半丁、秦仲文都给我们上过课。
除了共同课,多数时间还是老师在课堂上亲自辅导,雪涛先生就给很多同学改画完的作业,有时还现场示范。以画月季为例,月季的叶子很琐碎,极难处理,他却很轻松地点花头、点叶子,像满天星那样全纸落笔;到最后,借助枝干穿插在一起,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那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神奇,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