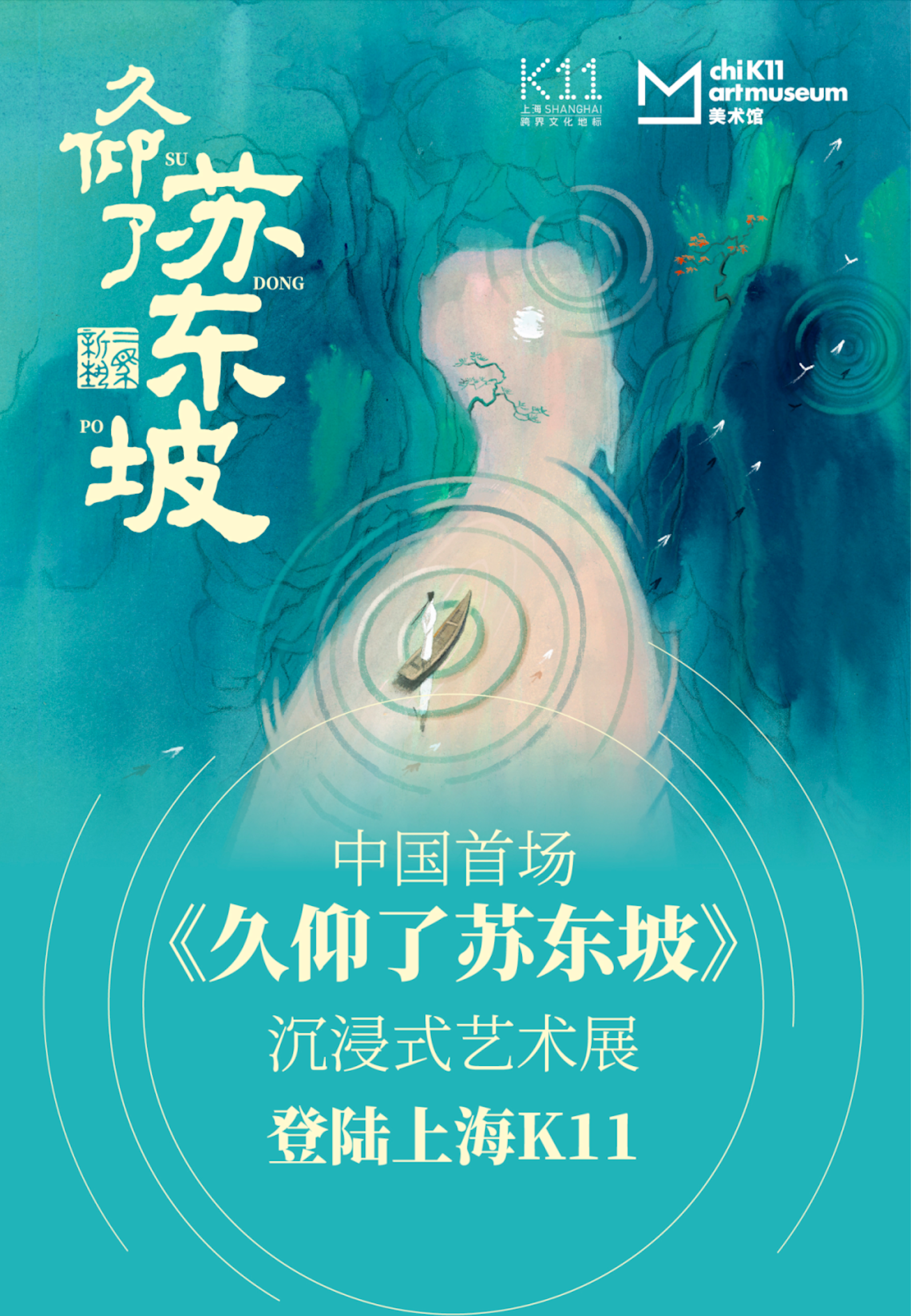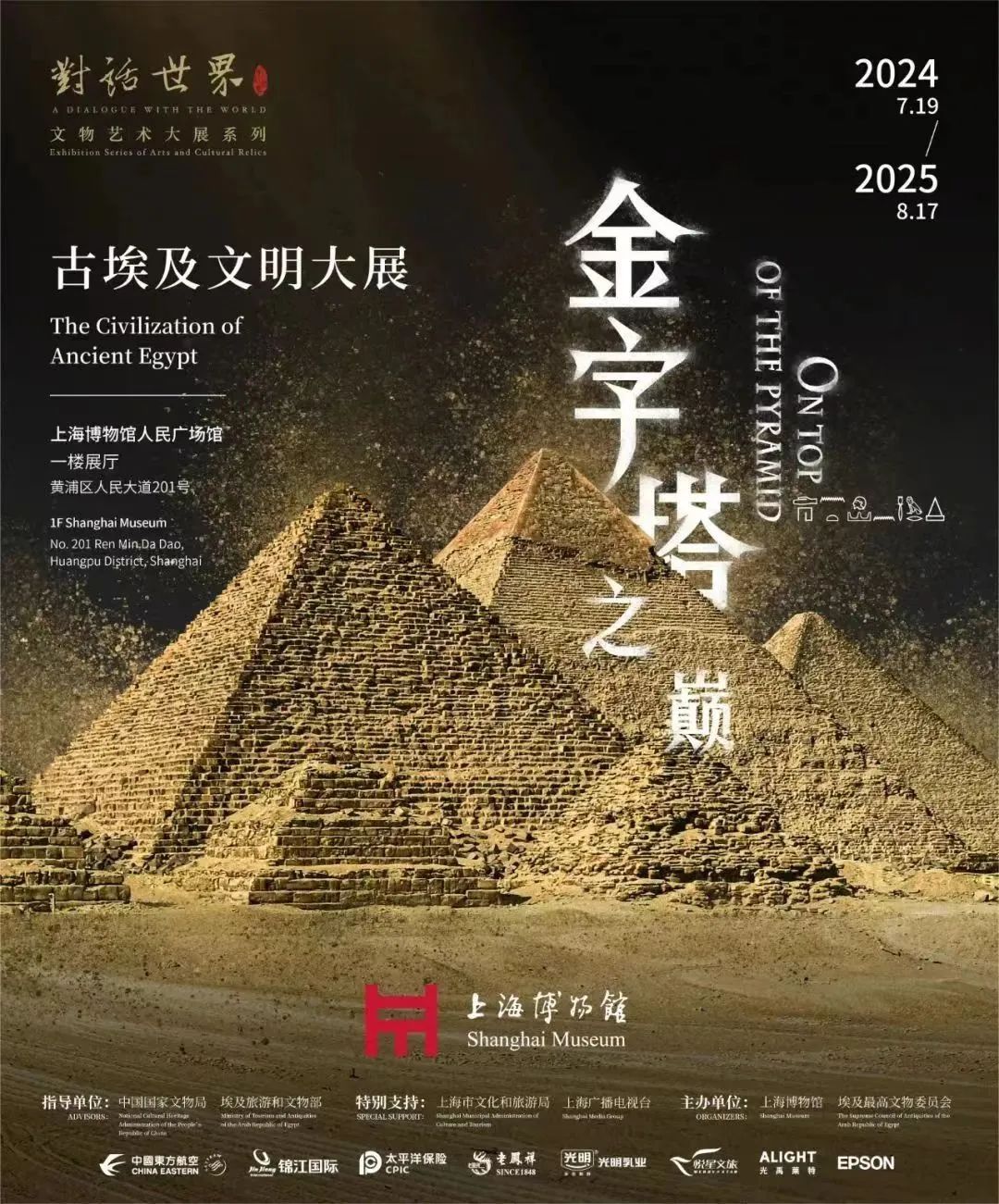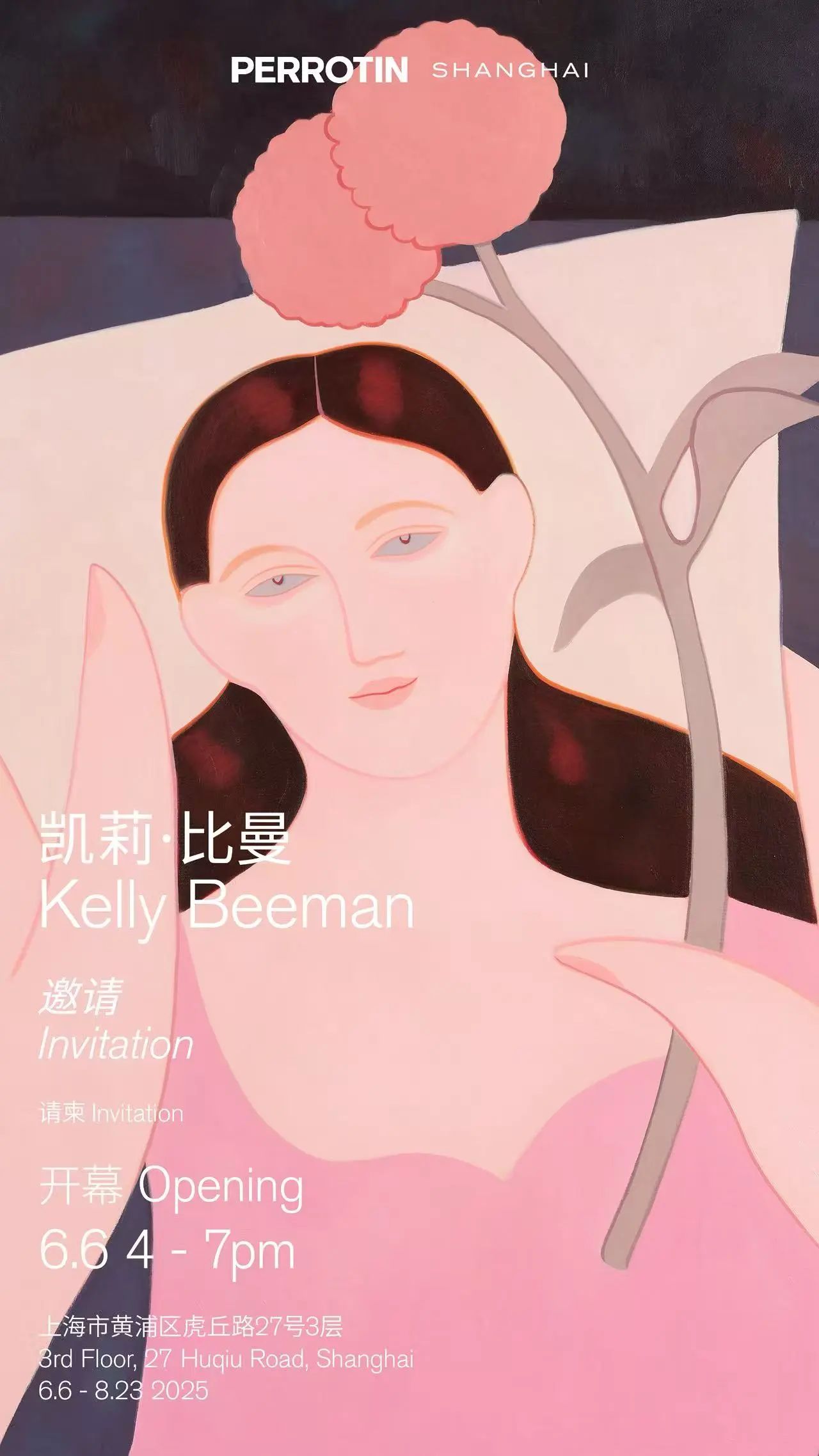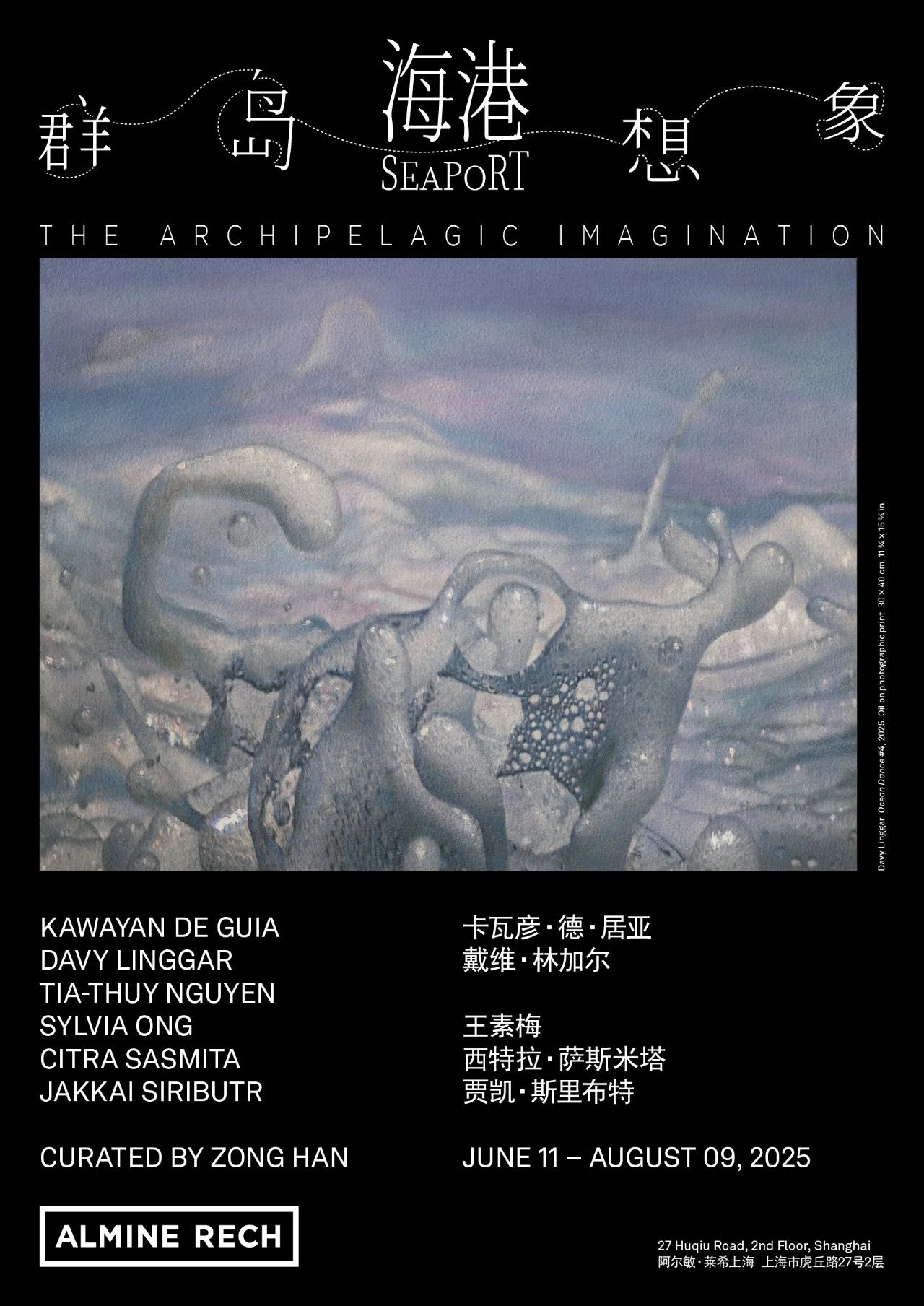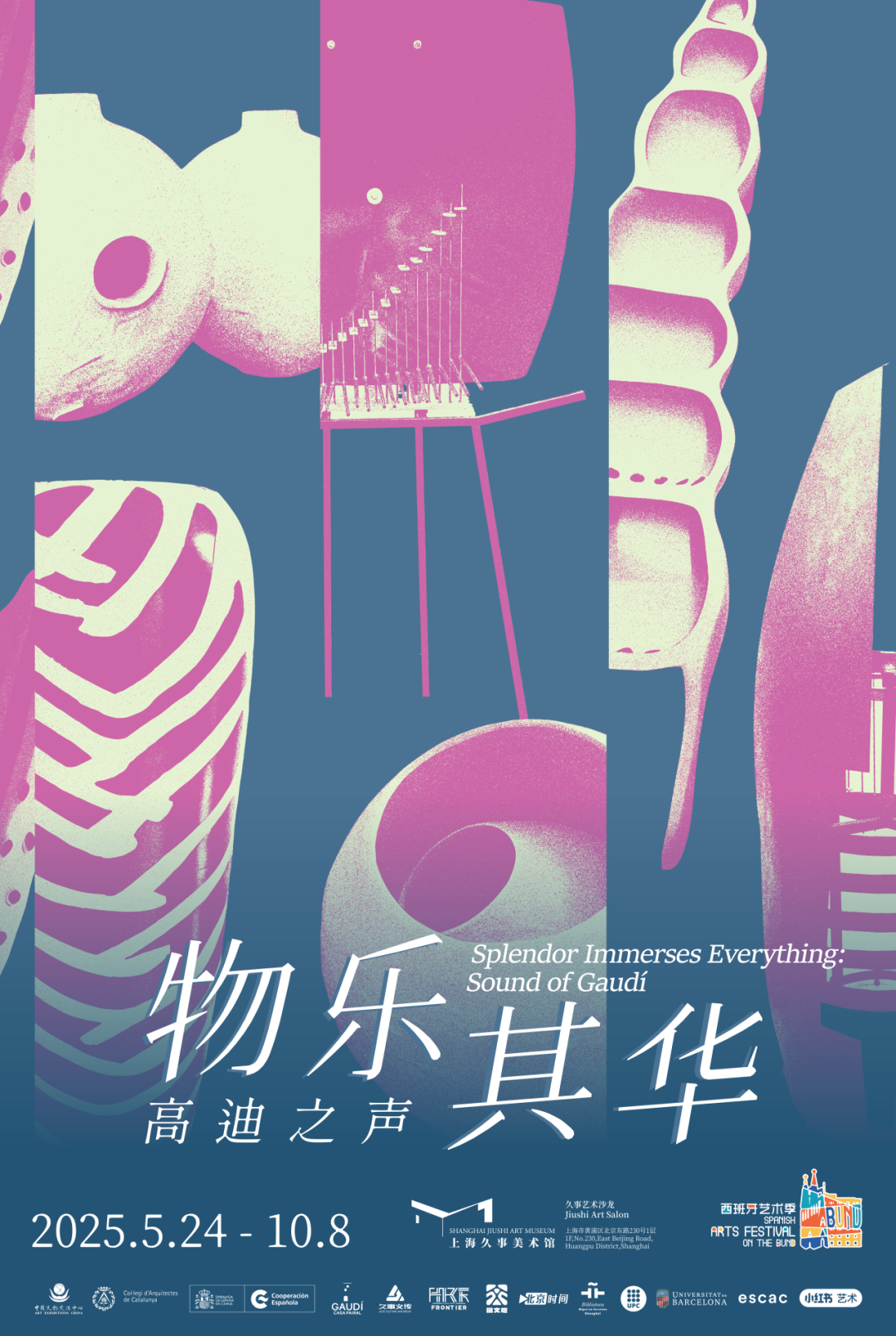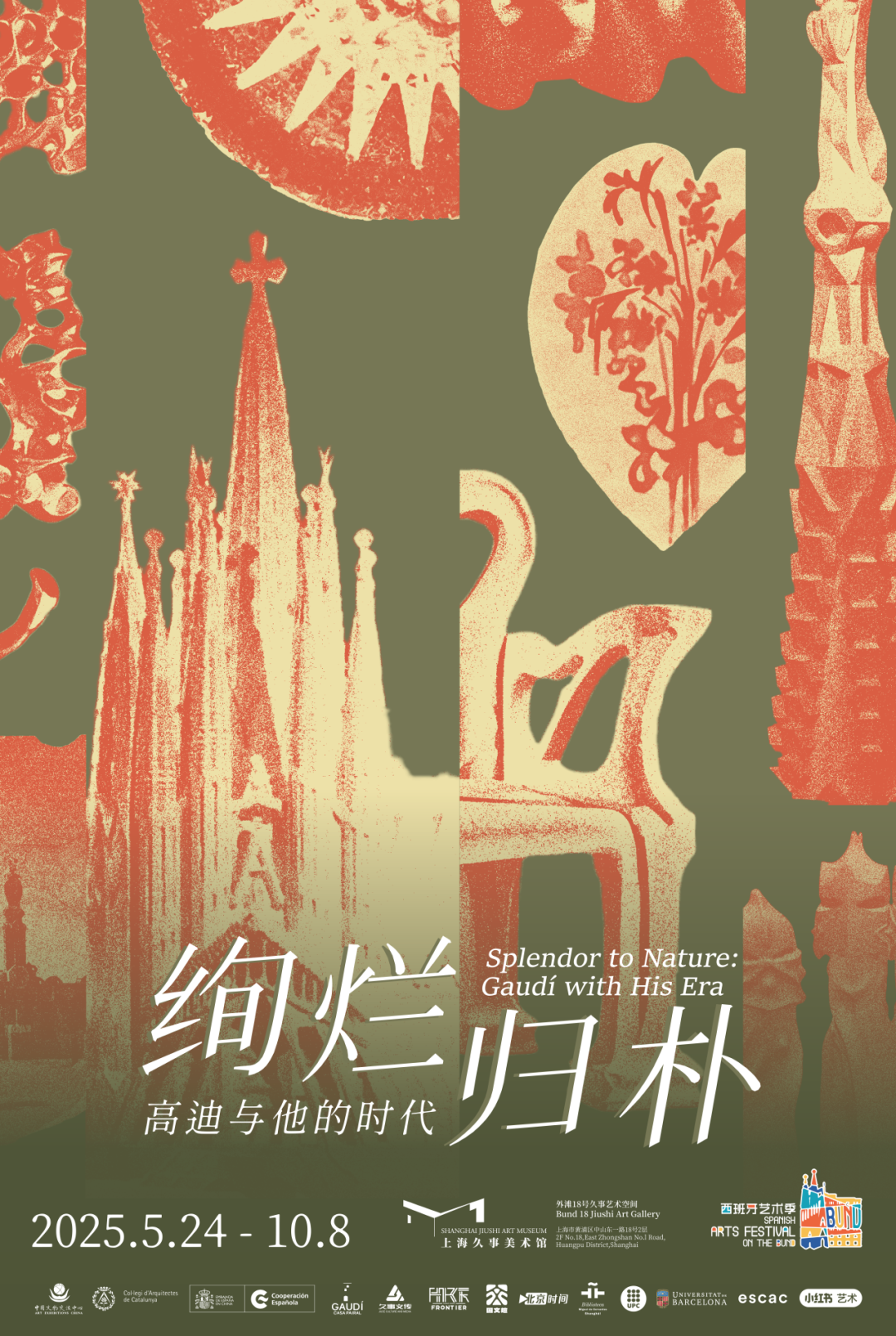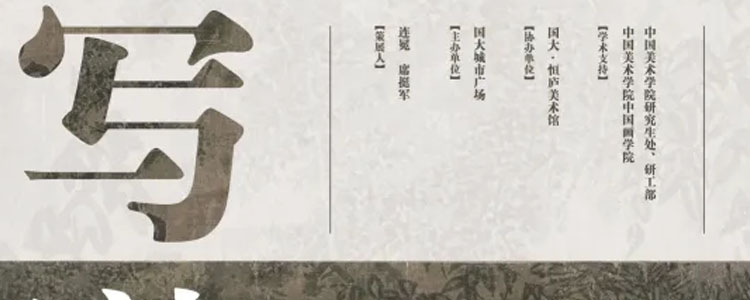
关于写神的创作至今我们还乐于带着历史的眼光来观看,也乐于将当前的和传统的展开优劣比较,或者转向中西技法的讨论,欣赏者、创作者更以此掂量、评断。不过,就作品的生成上看,这类比较式的背景话语实际是在询问:“到底怎样才是中国,如何方为中国人”。当前正在展出的所有成果,正以满溢着精妙笔力的别致表述,试图回答这组问题。
当然,我也期待观者不必苛求艺术家,话语的叙述本质上源于内心,创作者能为我们提供的,恰恰是其人自我的内观审视。不过,现在的评论还乐于引申着指向“宏大叙事”层面,这点倒要谨慎,乃至警惕。警惕的是,即便谈得那般宏大,其结果无非是让生命为不断被假象构拟出来的“艺术形式”服务。现实中,我们更期待真实的承继与传习,切肤的创作与革新,至于对世界和宇宙新的启示,这不是必然的选项,更不可能透过草草几笔、匆匆几眼便告实现。换言之,我们需要更多地回归那种与“大我”协调、进步着的真实“小我”。
同时,经济的发达一度对创作有着强烈的“垄断”,似乎操纵了画者形式表达的全程,这也是我们警惕“宏大叙事”的另一个因由。反观“真艺术”的本然面貌,是以哪怕最微末笔触都可充分阐发出最平凡的日常,而所谓“形式”,仅乃艺术人内心表达的载体和依托。辩证地说,叙述美好而细密的情愫,在画者,又正是借由不同境遇中对形式持续的淬炼而达成。不过,须注意的,是其内核最终还要回到讨论“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之中。一切创作的起点和终点应即如斯,而“形式”无非在奋力地呈现它们。创作者能做到这般,便无愧于己,也无愧于社群。循着前述的发问,即艺术人如何介入世人的内心,并密切地同他们的新生命联结起来,这才是最值得思考的目标终极。
画者的工作是提供一种与视频、影像完全迥异的图示维度,其间的历史性不是必然的附加品,艺术人本身个体化的“思考”方为社会集体思想的必然构成要件,继而证明“画”与“人”的持久。所以,创作者不可能脱离周遭,形神之妙也是得于日常。那么,所谓突破“生活的桎梏”,亦非孤立创作者的人格和性命,如此的表述千百年来一以贯之,从未更迭。得此真谛的佼佼者,因之方可于人类群星中闪耀,或伟岸、或高蹈。
由是,必须确认,关于创作的一切是基于个体和具身的,断非虚幻与设想。这不是建立粗糙的膜拜,却是希冀着铺排出属于人的,能证明其之存续的那个过程。而画者的苦斗,正是在此过程中,勤劬地寻觅新的、属于自己的语汇,以成功揭示出乳养着他们的世纪之情。
连 冕
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