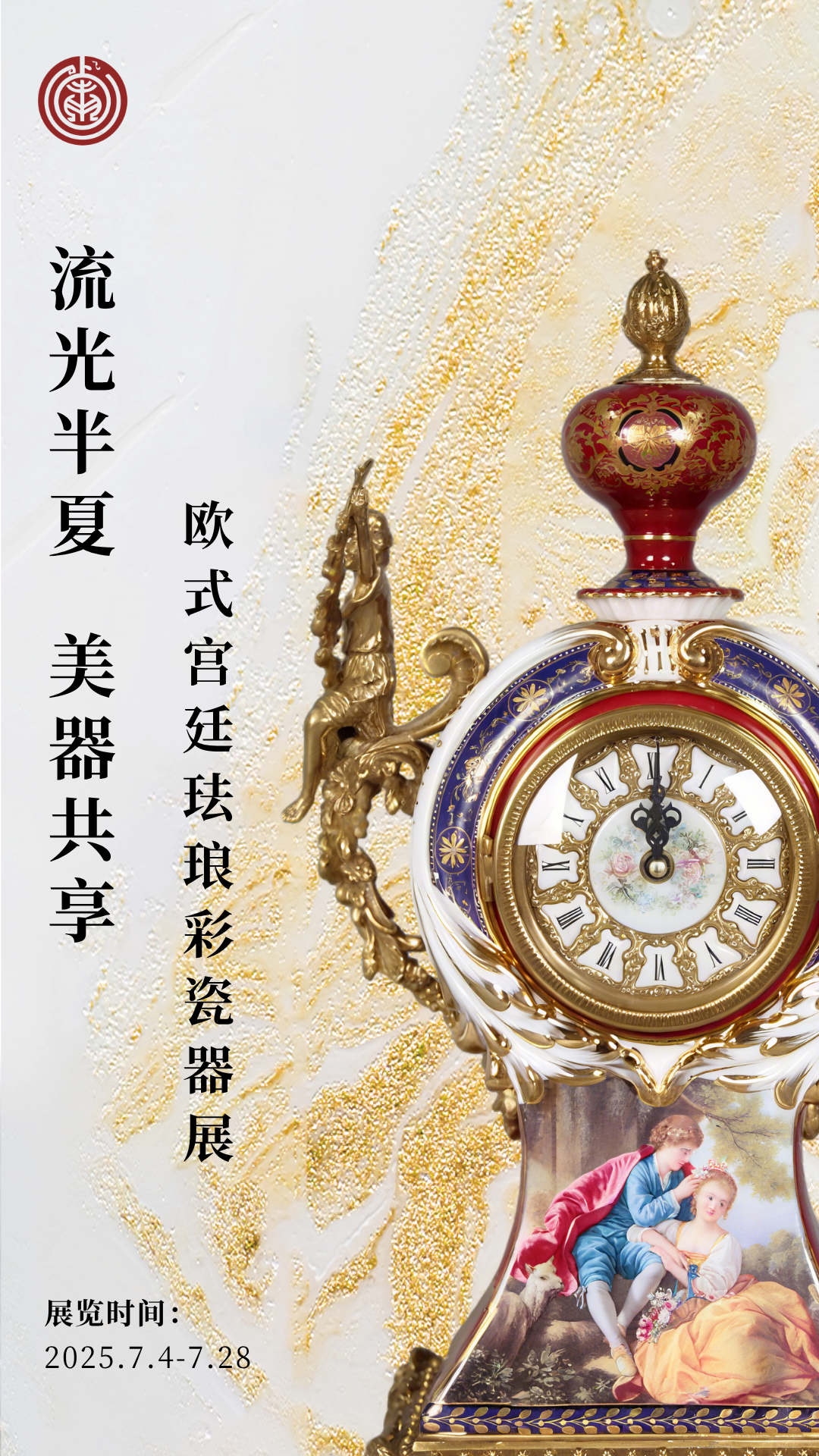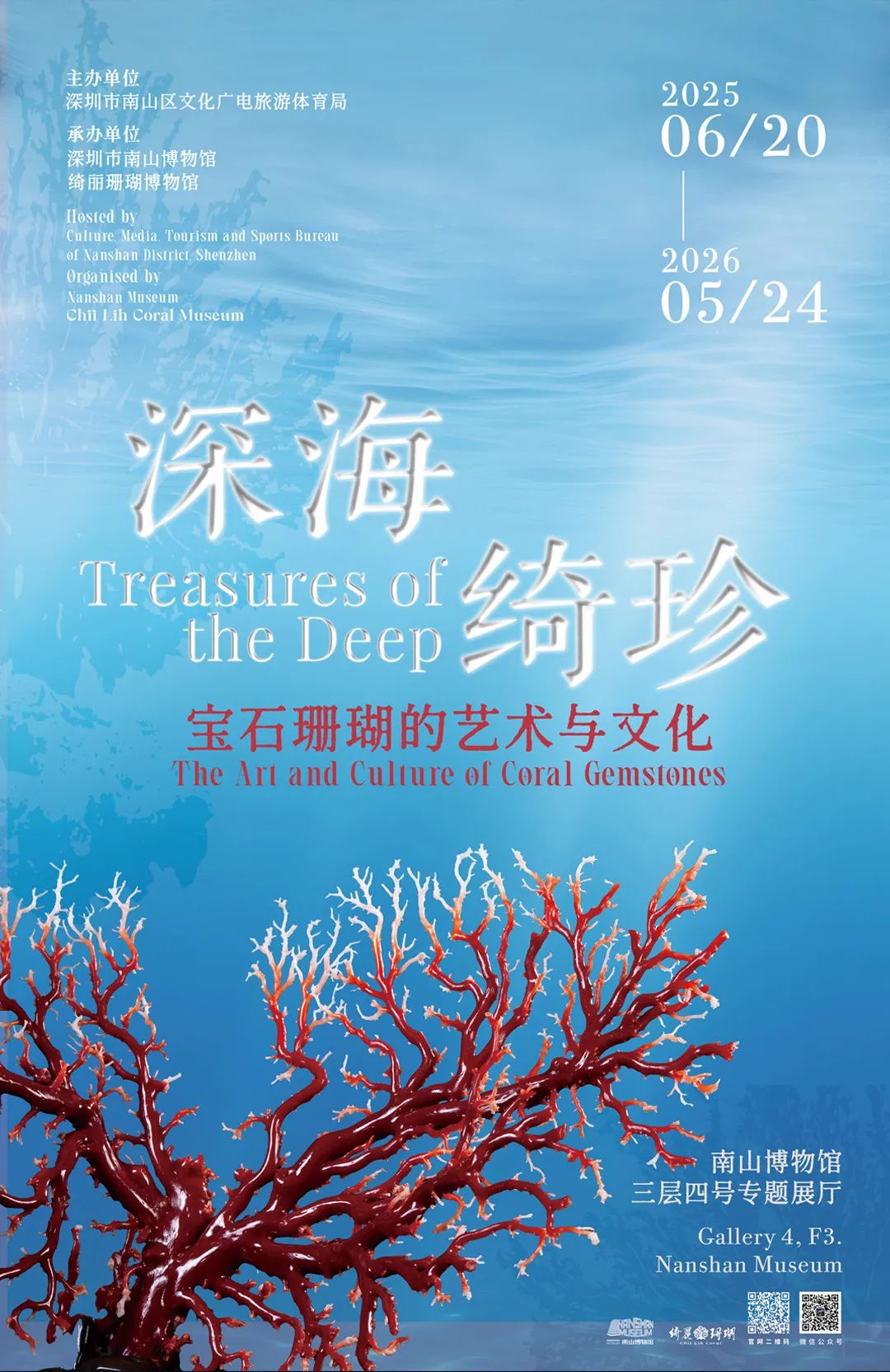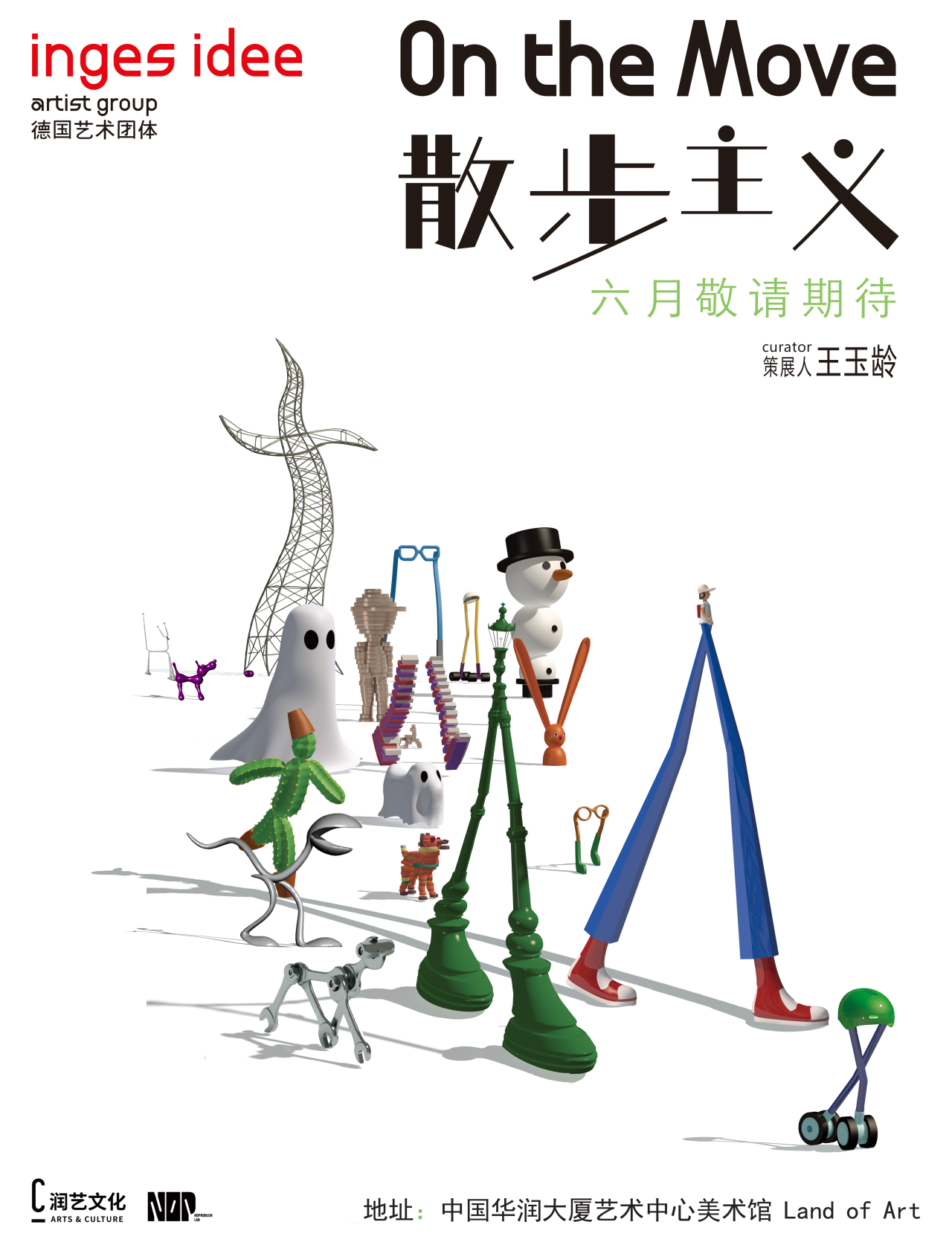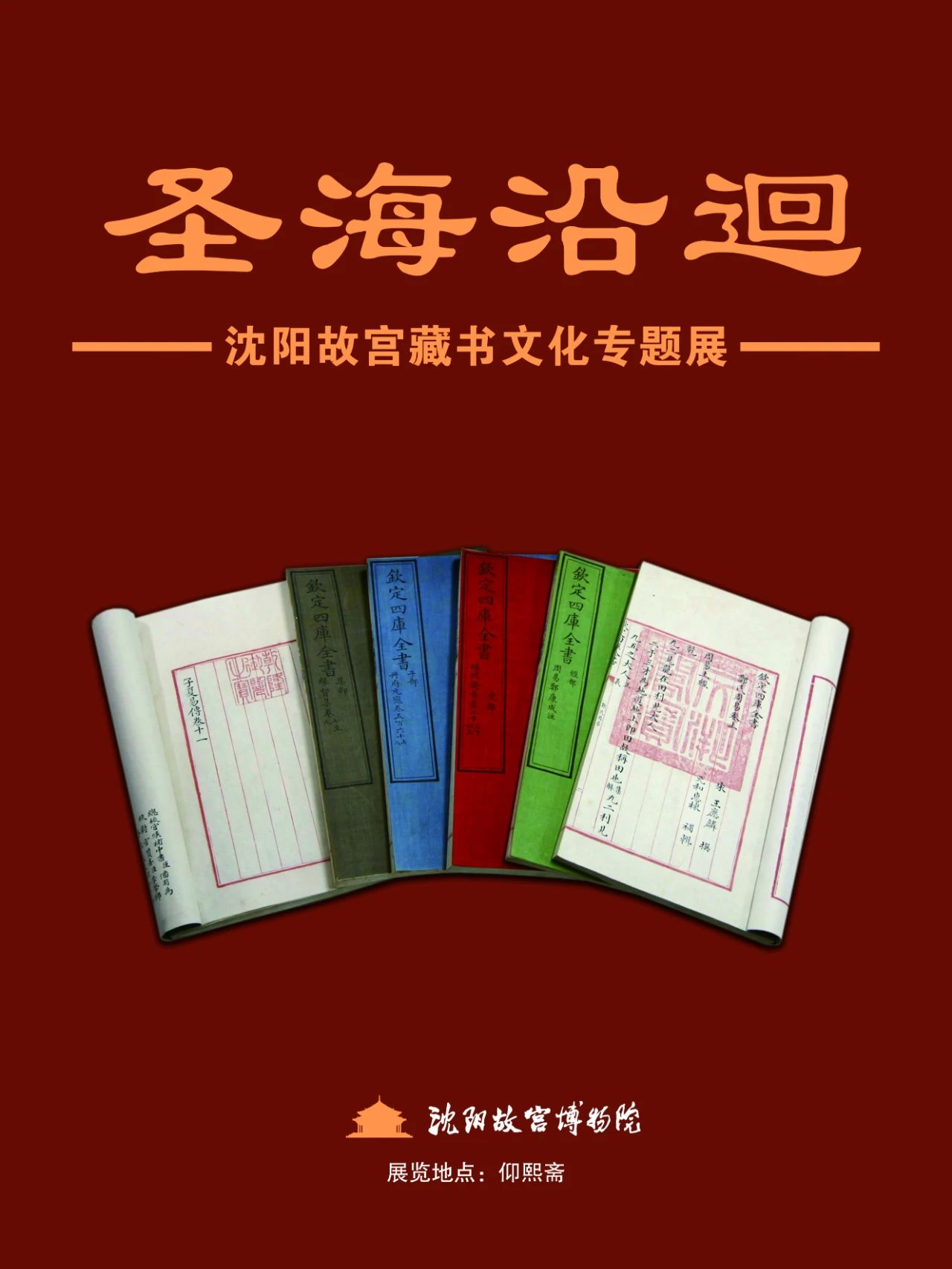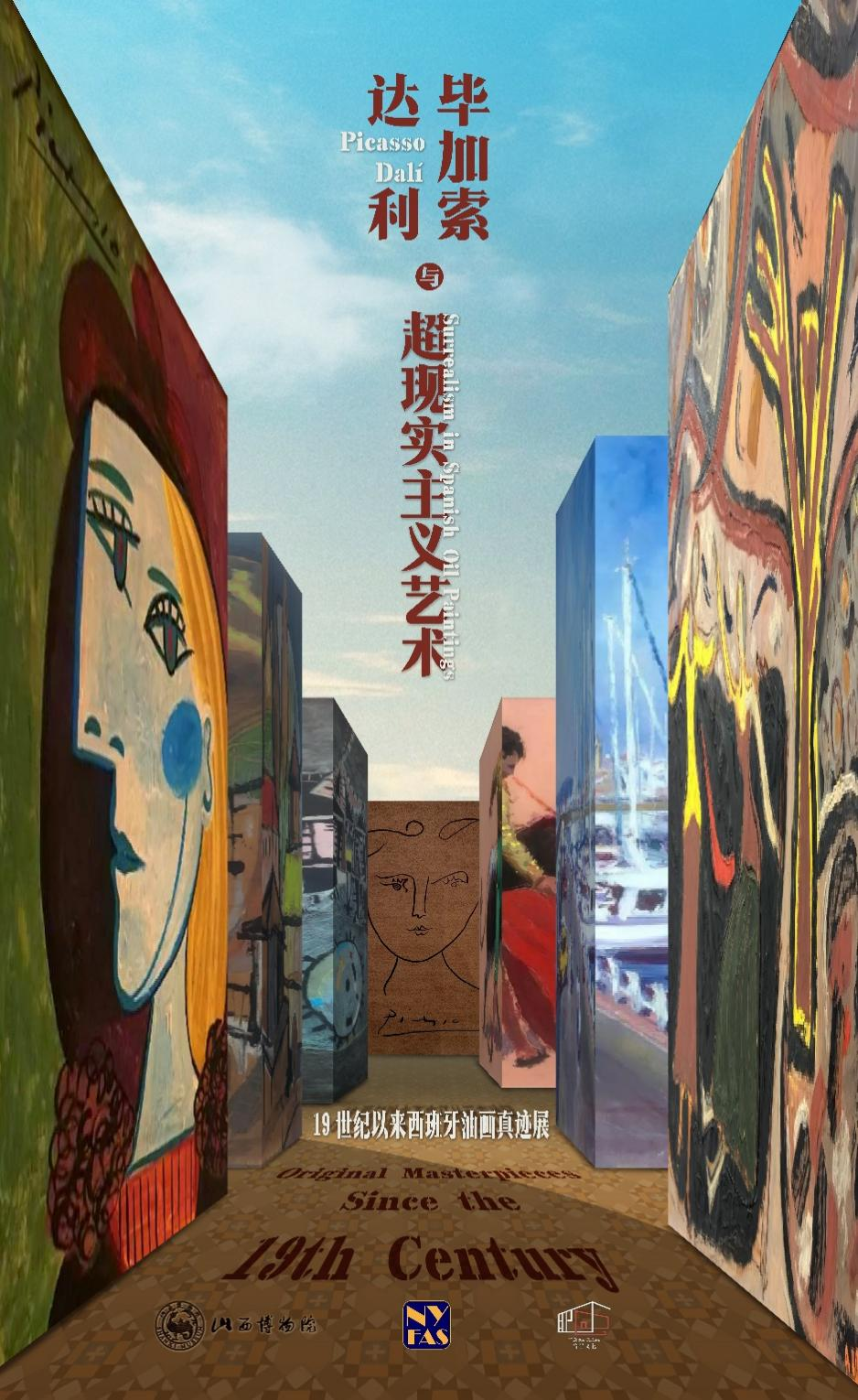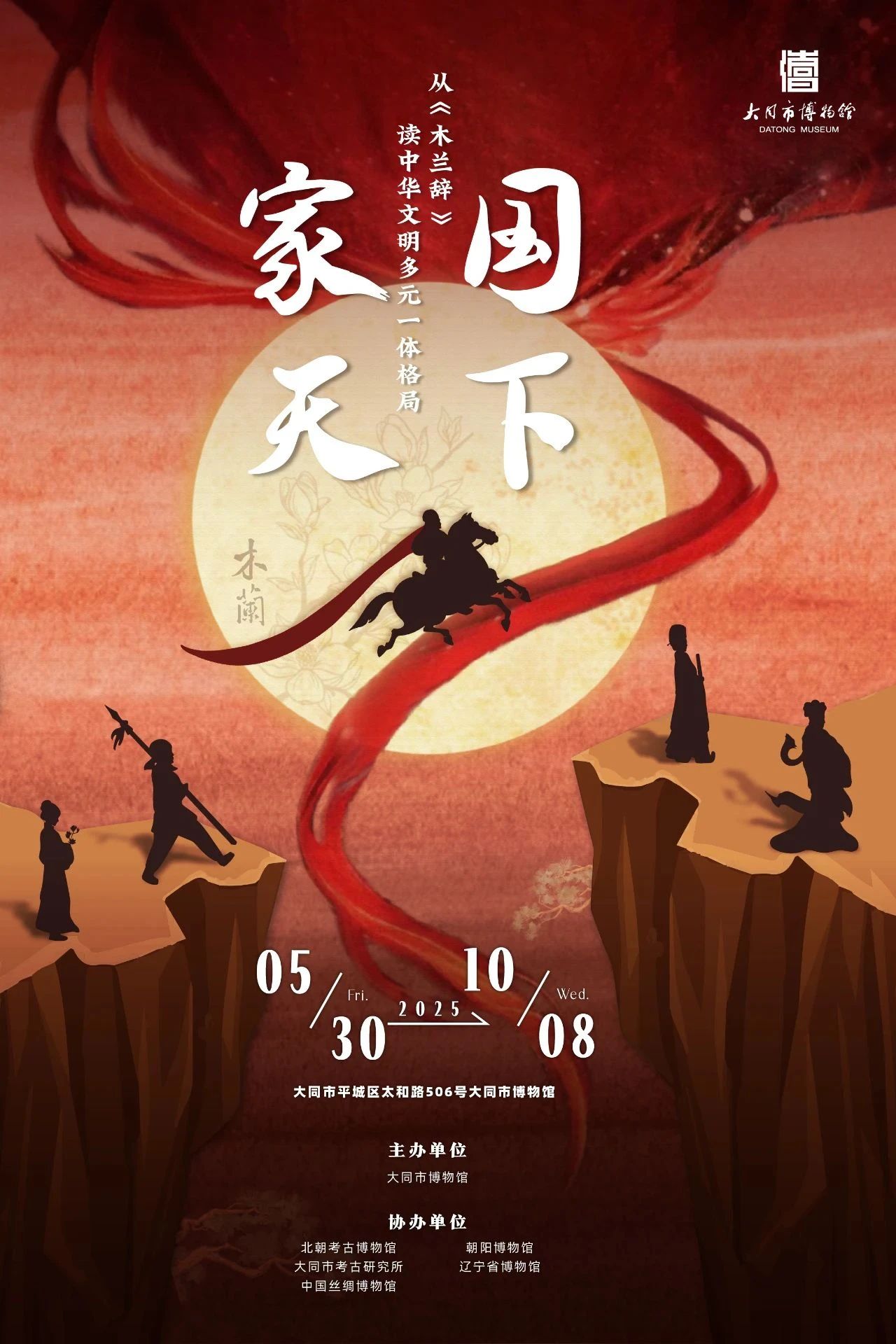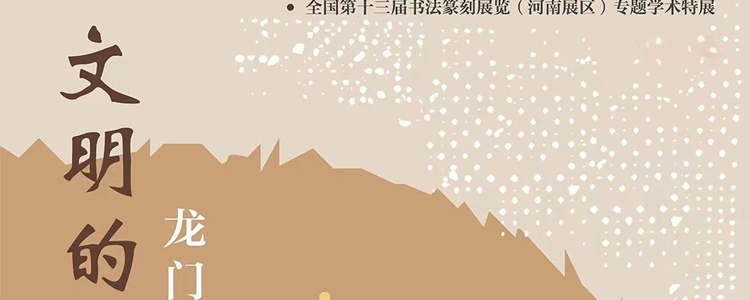
前言
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与书法遗存为后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资料。然通过考察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的传播历史,发现学术界对其价值的认识要远远滞后于其他的石刻文献。根据现存资料来看,最早对龙门石窟造像题记进行关注的,当始于欧阳修的《集古录》其在书中说:“ 右《三龛记》,唐兼中书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书,字画尤奇伟。在河南龙门山,山夹伊水东西可爱,俗谓其东曰香山,其西曰龙门。龙门山壁间凿石为佛像,大小数百,多后魏及唐时所造。惟此三龛像最大乃魏王泰为长孙皇后造也。”其后,赵明诚的《金石录》亦对《三龛记》进行了著录。但《三龛记》的本质还属于刻在山壁上的碑碣,其碑额题名亦称 “ 伊阙佛龛之碑”与真正意义上的造像题记有着根本的区别。
而真正意义上对龙门石窟造像记进行著录的,则要从比欧、赵晚了 500 余年的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开始,书中收录龙门石窟“ 武平六年造像记”一件,并评论道:“ 书法差可,画方格如棋局,而其半已磨灭。”此后,一直到了乾隆三十三年 (1768 年),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收录《杨大眼造像记》一件,才标志着学者们对属于后来《龙门二十品》中诸造像记的关注。之后,乾隆四十四年(1781 年),《潜研堂金石跋尾续编》收录《孙秋生》一件嘉庆四年 (1799 年),《潜研堂金石跋尾又续》收录《齐郡王元花》一件。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年) 河南巡抚毕沅所著《中州金石记》收录《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元燮>四件。武亿《授堂金石跋》收录《杨大眼》《魏灵藏》两件同一时期,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说:“龙门之山,伊阙之内石刻佛像最多,皆有姓名与造像年月,俱北朝人为君亲祈祷之意,愚而渎者也,字亦丑劣不足观。惟《杨大眼》以名将题名为世所重,其他碑中略有文词者,碑首两侧俱雕蛟龙之形,明季犹存七十二座,故相传为七十二座蛟龙碑余收藏大业、开皇、长安、武平、景明、孝昌等石像记仅二十余种。”可以看出,当时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还是以名人造像题记或“碑中略有文词者”为主,而《龙门二十品》中的《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为《龙门四品》的首先出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