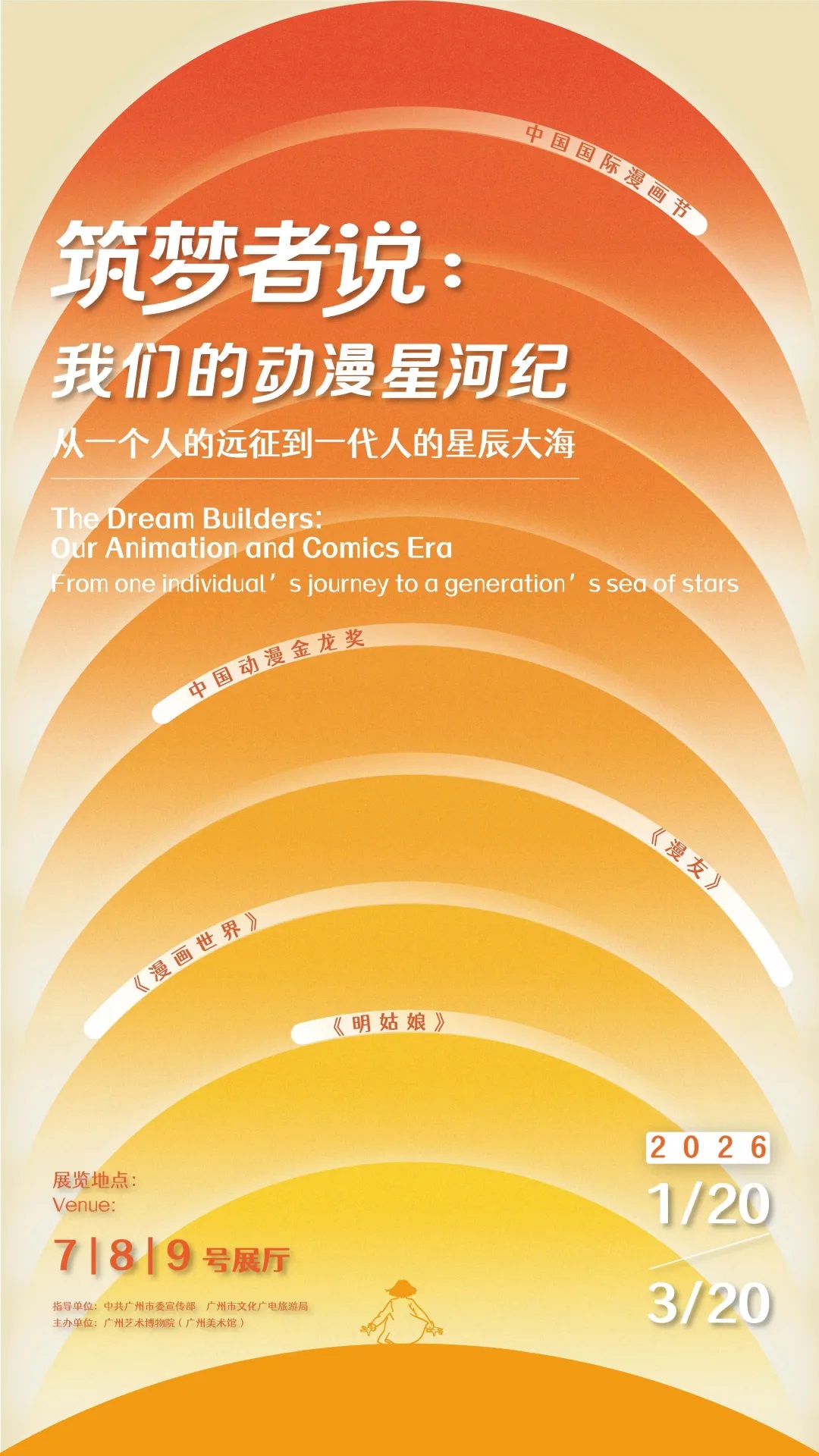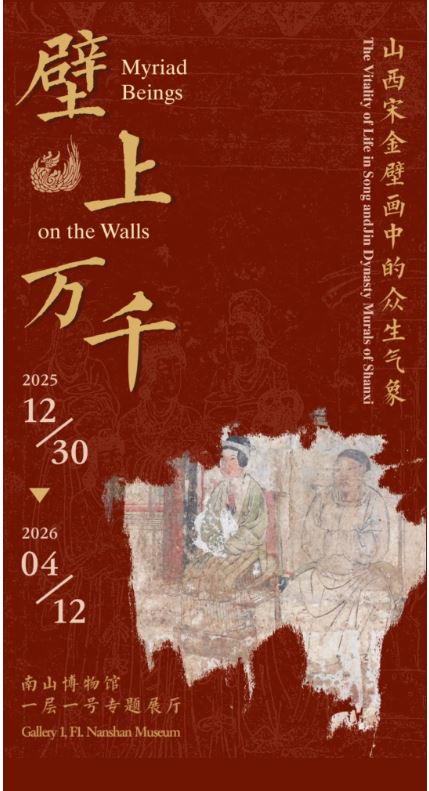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1923)对剧目《玩偶之家》中娜拉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遭遇所作的批评随笔:舞台之上的娜拉起初满足的认为自己在波谲云诡的社会大潮中找到了置身之处,伴随着对话与自白,娜拉一次次沉湎又自省于自身的遭遇,并终意识到“不单自己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玩偶也是,引申开去,就是别人怎么指挥,她便怎么做就是……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
时至今日,伴随着时代坐标的横移与个体价值的变化,我们将“娜拉”的出走和彰显个人价值的讨论,延展至当代艺术家在更广泛的整体性技术热潮中所经受的影响和做出的调整之上。在技术浪潮的冲刷下催生的复杂多变的媒介形式,导致了媒介边界上的模糊性和难以辨别的视觉特征,然而,人与工具的关系绝非“主人-奴隶”的二元对立的宿命论关系,一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 2015)在“玻璃牢笼”概念中提出的,在有关技术解放的夸赞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劳动者的蔑视,例如先进的机器和软件作为技术的产物,快速进入了日常化的场景中,随之引发的却是人作为劳动创造者对自身的怀疑情绪,“当飞行员在抱怨自动化时,抱怨的不仅是对技术本身的质疑,更是对于自我身份的探寻”——也便有了这一发人深省提问:他们是机器的主人,还是仆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
在当代社会生产力与技术媒介所参与构建的生产关系之间,“娜拉”对于主体性的持续争夺与强化似乎在漫长的时空中形成了某种对照,娜拉的出走令剧目戛然而止,但在帷幕落下的漆黑背后,时代的更迭和技术进步的浪潮从未停歇,也让社会文化生产的齿轮伴随着崇尚技术主义而不断加速,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和挑战着对于艺术家劳动价值的判断,也让基于前沿技术背景下的媒介与身体劳作之间形成了新一轮的被时代、社会和媒介革命所共同围拢的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