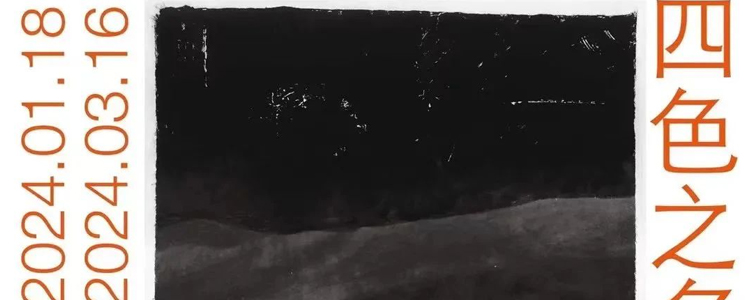
黄丹画很多事物,山、石、树、桥、马、猫、虎、兔、花卉、蔬果,这些传统中国画中亦有的题材被她反复捶打,变得愈发庄重,但同时又充满活力,她用一种今天的视角去描绘这些过去的,更确切的说,那些似乎一直存在而显得恒定的事物。近景、特写、满幅构图,在观看方式上,黄丹的作品与传统中国画的位置经营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她的画面具有镜头感,仿佛有一个观看者就在不远处端详。正是在这一点上,她的作品完全摆脱了“国画”的教化感,而生出了一种感性确实性的说服力。
但这种确实性并非视觉再现意义上的准确,实际上,黄丹减去了大部分的细节,在她的画中,事物通常只留下了轮廓与剪影,并孤伶伶的展现在虚空的背景前,变成了一个个的不依赖于定语的名词。它们既构成普遍类型,也极具个别性,即使很多形象简化到几乎是为了那几根线条而存在,但线条又因为它所依附的形象与形体而更具活性与动能,进而又反哺了形象与形体的活力。她简化造型、压缩体积、省略细节,这一切是为了把绘画的能量集中在线条、形状,以及绘画过程的时间厚度上,进而获得了一种碑拓式的钝力。
在色彩上,黄丹也极其精练,她几乎只使用墨色、赭石、朱砂、三绿等几种有限的颜色,因为在画面上只需构成明暗冷暖,即黑白丹青四色的区分,即可以表达万物。尤其是在她的作品中,平涂的色彩除了作为物像特征,更是作为形状的强化,让平面性获得更直接的锚定。
这让人想起地图学中的四色定理,即在一个平面上,只需四种颜色即可区分任意相邻的形状,黄丹用四种颜色去描绘一切,似乎也正暗合了这种最低限度原则。黄丹作品给人的最强烈印象就是她在色彩上的概括与节制,她的色彩并非只依据随类赋彩的再现逻辑,更多时候,实际上,有限的色彩选择让她更着意去推动这种限度下的可能,比如蓝色的马。
我们也可以从黄丹的作品中看到很多东西,除了活的事物,还有汉砖、魏碑、德加、马克(Franz Marc),还有丰子恺,换句话说,她的绘画不仅描绘了此时此地心之所见,更构成了一种回应着彼时彼地的风格,亦真理、亦德性,以四色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