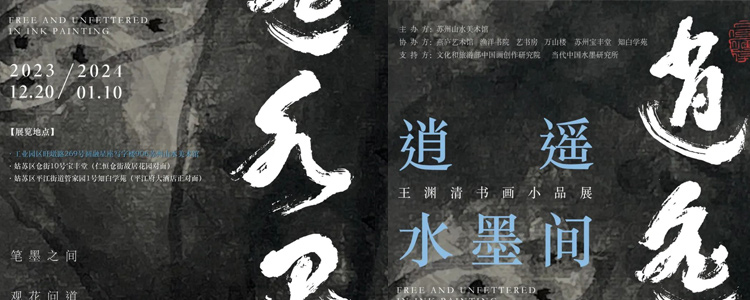
水墨画(即中国画)自20世纪初“美术革命”至20世纪末“笔墨之争”,可谓历经劫难和考验。
似乎每当风生水起之时,人们总是拿笔墨作为拷问对象。最终总是以牺牲笔墨作为条件而换取跻身现代、后现代艺术殿堂的入场券。
中国画的笔墨不仅作为本画种的基本技法,更是具有人格象征、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的多重价值体现,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尊之为金科玉律者有之,奉之为中国画底线者有之,视之为纯属技法者有之,斥之为阻碍中国画发展者有之,弃之为敝履者有之……
近百年来,人们逐渐模糊了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尤其是“清初四王”被指责为卖弄笔墨的形式主义典型,董其昌被批判为“罪大恶极”“葬送中国画四百年”,水墨画家们更是羞于表露自己对笔墨美的深深眷恋之情。只有黄宾虹在理论和实践双重领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主张:笔墨至上!
笔者经过三十余年的实践创作和理论研究,深深感悟到“笔墨乃中国画之本体”。
所谓“笔墨本体”之说基于双重的反思。从技法层面思考,中国画历来不重形似。从谢赫将“气韵生动”置于“六法”之首,到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倪瓒 “写胸中逸气”,再到徐渭“不求形似求生韵”,直至当代水墨画已将形似降低到极致。同样,西方现代艺术也忽视描摹对象写实性,而重视如何表现。抽象表现主义大师德•库宁就说:看一幅人脸的素描,要看的不是人脸而是素描。这与中国文人画轻形似重笔墨的审美论调如出一辙。
人们总是不断地追问,艺术家们为何要将描摹对象画得一点也不像,甚至于丑陋不堪。
其实,中国古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丑观,并解答了上述问题。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傅山“宁丑毋媚”的“四宁四毋”、刘熙载“丑到极处便是美”等皆为中华美丑观之经典。这里笔者引用西班牙奥尔加特的论述,也许更容易解开当代人心中的纠结:(艺术家)将我们封闭在一个神秘的空间里,迫使我们面对一些在现实中不可能面对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另创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面对世界、体验事物。我们必须别出心裁,才能适应那些奇妙现象。这种新的感受方式,这种去除自然形态后创造出的新方式,恰恰就是理解艺术、享受艺术。它们是绝对的审美感受。(西班牙奥尔加特•伊•加塞特《艺术的去人性化》)
从精神层面思考,中国画自古便承担了“明教义,助人伦”的社会责任。自“美术革命”以来,中国画更肩负了陶冶性灵、美育代替宗教,甚至拯救人类的重任。层层加码在中国画身上的重重重负,压得中国画步履蹒跚。事实上,艺术除了是艺术之外,他什么都不是;艺术除了对艺术负责,他什么都没用。倒是中国古代文人对自己的渺小有足够的清醒——一介书生!
艺术的当代性更是每一位具有担当精神的艺术家心中永远的牵挂。虽然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已成为画家们的口头禅,但众多画家和理论家们对艺术的时代性越发感到迷茫。毋须讳言,越来越多的水墨画家打着“崇尚笔墨”的旗号而纷纷走入了仿古、复古的不归路。然而水墨画的时代性肯定不是五六十年代画家笔下的烟囱、水坝,以及当代灯红酒绿的城市夜生活所能涵盖的。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笔墨的本体意义时,画什么已不成为问题;怎么画亦“退居二线”。只有表现什么才是水墨画家们殚思竭虑的当代性。
于是,当同道们一再催促笔者对水墨画下一简洁的定义时,笔者无奈地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水墨画就是水墨在毛笔的书写描绘中,在宣纸上留下的痕渍。这个定义让多少对水墨画充满期待的人感到失望或索然无味。然而只有卸除了强加在中国画身上的种种不能承受之重,揭去层层花俏面纱,还原一尊纯粹的、赤裸裸的水墨画真身。那时,我们才能真正欣赏到本真的笔墨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