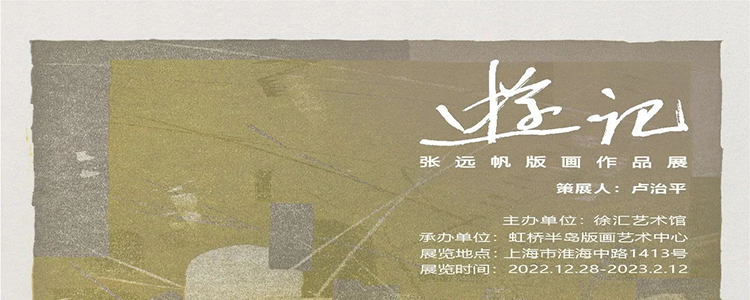
解名作序,难避刻意之嫌。但以“名”为词作指认时,其词意又总能粘连在那自然发生的依稀的情景之中:当激越的潮流平息,远处的帆影投射出“远行”或“回归”的意象,顷刻间,跌宕起伏的自我思绪被转化为平和的画面。我想,远帆老师的艺术从这里开始,也许是适时的吧。
因远帆老师之“名”,而纪念另一位张老师——张怀江先生的木刻成就,也是顺理成章的。远帆老师其家学中有木刻传承,它见证了新中国版画的演变与发展历程。倘若这样溯源,从“完善技法的大众化”到“合主题的内化”,再到版画的解放或艺术形式的确认,昭示出两代版画家播撒的希望。那么,“远帆”之名,即是前辈的寄托。
远帆老师的贡献,落在了他对形式的判断上,形成了远帆版画的图像修辞。
一般的,“远行”和“回归”都和“游”、“旅”相关。“游”是“流人远放”寓言式的凝视,潜伏于文化深层想象之中;“旅”,则象征着有具体的行动。远帆老师说:他“表达的多是内视的所见,即时的情绪,心境况味的显现,是问心的答案”。这反映在作品《游记——碑廊》里,就不见了具体的地点、事件和时间,而仅存的,是在标题提示下隐隐呈现着的对象。
若只从物的指认到图像的形式阐发为路径,这种描述会变得索然无味。我们还是回到画面:清冽的白色划线,像极了时间的符号,又似是速度的暗示;隐在线背后的碑、廊,被从容地挤压在黄昏暮色的联想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色层中透出的略带粉色的残梦,用叠压着纷乱情绪的线条,诱向冥想的空间里,形成了浑然天成的迷思。
游记——弄堂——碉楼——风痕——故苑——蜃门——寒村——深院——偏门——秘门——观塔, 这一条“物”的检视链,或许是为观者的预期而设定的,但对他而言,《游记》则是一种心境的通道。所谓“游,旗旌之流也”,暗示着一种自由无拘束的运动。想象的、没有目的的行为,如目游,神游等,而非西方解构主义式的破坏和消除。“行游”,只有当遭遇异域的陌生的异质文化时,才会以一种感觉来描述另一种的感觉,勾连起新的修辞方式。
2002年冬,远赴法兰西的远帆老师收获了属于他的《游记》——“随心而行、随行而遇、随遇而悦”的“行远”体悟。和前贤们一样,唤醒了自证身份的生命思考。也即是说,思想游记是“熟稔化”错位的思考与阐发,是他选择从弄堂漫游到塔楼的指南,折射出内心深处的精神回归。
“游”即是诗,传统的身体行旅,变成了精神的漫游,是由“观想”所引发的书写意境。游与隐,记与诗,言与志,回到山林消除杂乱纷争,隔离现实的枯燥,在沉淀与移情中呼告,这是我对游记体的理解。其实,远帆老师承接的并不是出游的欲念,而是以内化的情感抒发为线索,应用了游记文本传播的特质,产生了亲历者在处理材料过程中,把握着的陌生角度,造成了回环式往复的形式穿梭,使散片化的抽象思路得到整合。
书写的诗文意味,自然介入于图像制造之中,这一点似有唐代诗人寒山的意趣:“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寒山把诗和诗境合二为一了。他在诗中结构了新格律,用平淡自然透露质朴的自我化的情感。作为“行”与“观”的即时组合,让游记记录在现场。胡适有言:“应该问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这也是确切的。
东方看见了“禅”,西方发现了“人”。今天,我们看见了《游记》的观想,从“镜像”的结构中又重拾了诗文。
中国文人的“诗画”与西方的“诗学”,并非存在于同一个观念中。但《游记》的散文诗体,如修辞中的“示现”般存在着相互关联,如见如闻。是由看,到呈现方法所引起的诗兴的冲动。
远帆老师的版画,从诗性的角度,解构了作为再现功能的图像表现。他从物象的光阴中,执意提取出斑驳的光点,使图像生成了似是“数码”脱显的效果。图像辨认变为元素的辨认,再用刮蹭的方法去“刀迹化”,使画面深度空间在克制中形成了拟图片的平面样式,让所谓的“刀法”成为书写的工具。
他的“减版套印”,实践着“刻印”的随意性,让“痕迹”与“游”的主题共生,即由版对版的叠加中思考图像走向。解放了用“塑形”来“达意”的复现手段,把手迹、印痕最大化,重构了作为“漫游”的意象,产生了情绪游离瞬间,继而追问起短暂的时光。
我喜欢读远帆老师的《关于游记》和写于巴黎的《我和我的游记》。我是依据其意引申到他的版画。在这些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游记体作品里,他把感受游历的过程作为方法,介入到版画探游之中。让技术的神游与意念的放纵,建构在空间的想象中,这样的坚持,反映着始于文化源头的思想回归方式。
百年前,法国诗人也是游记作家谢格兰,曾在中国写下以《古今碑录》为名的诗集,其装帧即是西安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样式的缩版。他为此写道:“它们一经嵌入石碑,就用它们的智慧渗透了石碑,就脱离了人类那动荡不定的理性形态,变成了石头的思想,具有了石头的质地。……它们不表达,它们示意,它们存在 ”。
石碑与木刻不同,碑与碑、廊也不同,但它们都在那里了,这也是事实。
因远帆老师之“名”,而纪念另一位张老师——张怀江先生的木刻成就,也是顺理成章的。远帆老师其家学中有木刻传承,它见证了新中国版画的演变与发展历程。倘若这样溯源,从“完善技法的大众化”到“合主题的内化”,再到版画的解放或艺术形式的确认,昭示出两代版画家播撒的希望。那么,“远帆”之名,即是前辈的寄托。
远帆老师的贡献,落在了他对形式的判断上,形成了远帆版画的图像修辞。
一般的,“远行”和“回归”都和“游”、“旅”相关。“游”是“流人远放”寓言式的凝视,潜伏于文化深层想象之中;“旅”,则象征着有具体的行动。远帆老师说:他“表达的多是内视的所见,即时的情绪,心境况味的显现,是问心的答案”。这反映在作品《游记——碑廊》里,就不见了具体的地点、事件和时间,而仅存的,是在标题提示下隐隐呈现着的对象。
若只从物的指认到图像的形式阐发为路径,这种描述会变得索然无味。我们还是回到画面:清冽的白色划线,像极了时间的符号,又似是速度的暗示;隐在线背后的碑、廊,被从容地挤压在黄昏暮色的联想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色层中透出的略带粉色的残梦,用叠压着纷乱情绪的线条,诱向冥想的空间里,形成了浑然天成的迷思。
游记——弄堂——碉楼——风痕——故苑——蜃门——寒村——深院——偏门——秘门——观塔, 这一条“物”的检视链,或许是为观者的预期而设定的,但对他而言,《游记》则是一种心境的通道。所谓“游,旗旌之流也”,暗示着一种自由无拘束的运动。想象的、没有目的的行为,如目游,神游等,而非西方解构主义式的破坏和消除。“行游”,只有当遭遇异域的陌生的异质文化时,才会以一种感觉来描述另一种的感觉,勾连起新的修辞方式。
2002年冬,远赴法兰西的远帆老师收获了属于他的《游记》——“随心而行、随行而遇、随遇而悦”的“行远”体悟。和前贤们一样,唤醒了自证身份的生命思考。也即是说,思想游记是“熟稔化”错位的思考与阐发,是他选择从弄堂漫游到塔楼的指南,折射出内心深处的精神回归。
“游”即是诗,传统的身体行旅,变成了精神的漫游,是由“观想”所引发的书写意境。游与隐,记与诗,言与志,回到山林消除杂乱纷争,隔离现实的枯燥,在沉淀与移情中呼告,这是我对游记体的理解。其实,远帆老师承接的并不是出游的欲念,而是以内化的情感抒发为线索,应用了游记文本传播的特质,产生了亲历者在处理材料过程中,把握着的陌生角度,造成了回环式往复的形式穿梭,使散片化的抽象思路得到整合。
书写的诗文意味,自然介入于图像制造之中,这一点似有唐代诗人寒山的意趣:“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寒山把诗和诗境合二为一了。他在诗中结构了新格律,用平淡自然透露质朴的自我化的情感。作为“行”与“观”的即时组合,让游记记录在现场。胡适有言:“应该问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这也是确切的。
东方看见了“禅”,西方发现了“人”。今天,我们看见了《游记》的观想,从“镜像”的结构中又重拾了诗文。
中国文人的“诗画”与西方的“诗学”,并非存在于同一个观念中。但《游记》的散文诗体,如修辞中的“示现”般存在着相互关联,如见如闻。是由看,到呈现方法所引起的诗兴的冲动。
远帆老师的版画,从诗性的角度,解构了作为再现功能的图像表现。他从物象的光阴中,执意提取出斑驳的光点,使图像生成了似是“数码”脱显的效果。图像辨认变为元素的辨认,再用刮蹭的方法去“刀迹化”,使画面深度空间在克制中形成了拟图片的平面样式,让所谓的“刀法”成为书写的工具。
他的“减版套印”,实践着“刻印”的随意性,让“痕迹”与“游”的主题共生,即由版对版的叠加中思考图像走向。解放了用“塑形”来“达意”的复现手段,把手迹、印痕最大化,重构了作为“漫游”的意象,产生了情绪游离瞬间,继而追问起短暂的时光。
我喜欢读远帆老师的《关于游记》和写于巴黎的《我和我的游记》。我是依据其意引申到他的版画。在这些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游记体作品里,他把感受游历的过程作为方法,介入到版画探游之中。让技术的神游与意念的放纵,建构在空间的想象中,这样的坚持,反映着始于文化源头的思想回归方式。
百年前,法国诗人也是游记作家谢格兰,曾在中国写下以《古今碑录》为名的诗集,其装帧即是西安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样式的缩版。他为此写道:“它们一经嵌入石碑,就用它们的智慧渗透了石碑,就脱离了人类那动荡不定的理性形态,变成了石头的思想,具有了石头的质地。……它们不表达,它们示意,它们存在 ”。
石碑与木刻不同,碑与碑、廊也不同,但它们都在那里了,这也是事实。
2022年12月8日于西安美术学院

最新展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