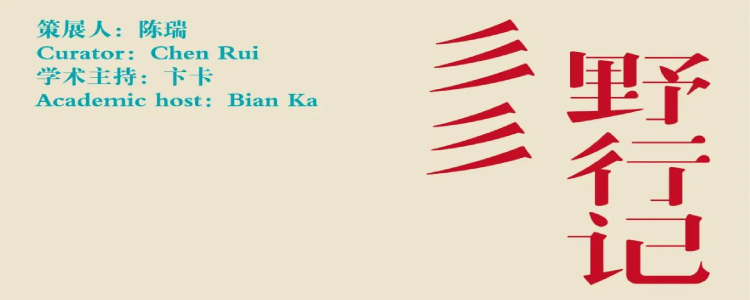
刘彤彬的野行记,是一场贯穿始终的艺术理念与艺术行动。
在若干年前,刘彤彬就在为这次“野行”做准备,因为他知道,只有勇气、信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并切合实际的方法。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都会涂上几笔,颜色基本上是金色、银色和黑色的马克笔,偶尔还会加入杂志撕剪下的图像粘贴在一起,这些手稿已经不仅是简简单单的写生的和速写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图像学的采集和分析,背后有着非常直觉化的判断,这些看似随意且碎片化的元素成为了日后的砖石。
“野行”是刘彤彬个人化选择,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回应。如同近年异常火爆的户外露营与徒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而现象的另一面,是普遍性的焦虑、内卷、精神内耗所结成的硬壳。余华说他写作经历了四十年的精神内耗,但在某种程度是件好事儿,没有内耗就没有思考,没有思考就不会有内心的悸动,所以余华总结精神内耗实质其实是一个寻找出口的过程,只要你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就会有内耗。我相信刘彤彬也有同样的经历,从他的艺术历程而言,尝试了多种材料、绘画手段以及观念的转换就可见一斑。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艺术上的出口,而野行是他属于自己的方式。
野行代表的状态,不仅仅是一次次的出走与自我放逐,除了寻找、探寻、漫游、出走、归来的一系列的过程和心境。更重要的是他在行动的过程中用怎样的艺术的方式去做了怎样的记录和表达。我想,刘彤彬的几十本手稿本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刘彤彬野行的方式是多元和立体的,除了以上所述的旅行与记录,还包括野外展览实践、绘画材料研究、田野调查、当代艺术的研究与传播等。尤其是围绕“射乌山”进行的系列当代艺术策划实践,将废弃的厂房和山野作为试验场,探讨城市化、消费主义、环保等议题,并拓展了策展理念与展览表达的可能性,令人印象深刻。在主持“水印版画技法与材料实验室”的过程中,从材料入手,追根溯源,逆流而上,对纸张、板材、工具等进行考察和研究,弥补空白的同时也建构了水印版画的底层土壤……这也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知行合一的理念在艺术实践中留下了清晰的注脚,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条路径在本次展览也融为一体。这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到刘彤彬此次展览以全新的面貌、材料和表达进行的呈现,并非心血来潮的转型,也不是灵感迸发式的宣泄,他一直在做这样努力,包括素材的积累、感觉的积淀、材料的探寻,最终整体而轻松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却又十分自然而然的创作状态。
在若干年前,刘彤彬就在为这次“野行”做准备,因为他知道,只有勇气、信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并切合实际的方法。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都会涂上几笔,颜色基本上是金色、银色和黑色的马克笔,偶尔还会加入杂志撕剪下的图像粘贴在一起,这些手稿已经不仅是简简单单的写生的和速写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图像学的采集和分析,背后有着非常直觉化的判断,这些看似随意且碎片化的元素成为了日后的砖石。
“野行”是刘彤彬个人化选择,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回应。如同近年异常火爆的户外露营与徒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而现象的另一面,是普遍性的焦虑、内卷、精神内耗所结成的硬壳。余华说他写作经历了四十年的精神内耗,但在某种程度是件好事儿,没有内耗就没有思考,没有思考就不会有内心的悸动,所以余华总结精神内耗实质其实是一个寻找出口的过程,只要你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就会有内耗。我相信刘彤彬也有同样的经历,从他的艺术历程而言,尝试了多种材料、绘画手段以及观念的转换就可见一斑。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艺术上的出口,而野行是他属于自己的方式。
野行代表的状态,不仅仅是一次次的出走与自我放逐,除了寻找、探寻、漫游、出走、归来的一系列的过程和心境。更重要的是他在行动的过程中用怎样的艺术的方式去做了怎样的记录和表达。我想,刘彤彬的几十本手稿本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刘彤彬野行的方式是多元和立体的,除了以上所述的旅行与记录,还包括野外展览实践、绘画材料研究、田野调查、当代艺术的研究与传播等。尤其是围绕“射乌山”进行的系列当代艺术策划实践,将废弃的厂房和山野作为试验场,探讨城市化、消费主义、环保等议题,并拓展了策展理念与展览表达的可能性,令人印象深刻。在主持“水印版画技法与材料实验室”的过程中,从材料入手,追根溯源,逆流而上,对纸张、板材、工具等进行考察和研究,弥补空白的同时也建构了水印版画的底层土壤……这也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知行合一的理念在艺术实践中留下了清晰的注脚,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条路径在本次展览也融为一体。这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到刘彤彬此次展览以全新的面貌、材料和表达进行的呈现,并非心血来潮的转型,也不是灵感迸发式的宣泄,他一直在做这样努力,包括素材的积累、感觉的积淀、材料的探寻,最终整体而轻松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却又十分自然而然的创作状态。
前言/陈瑞
上一篇: 月亮的倒影是海的脊骨
下一篇: 无垠降临——胡行易作品展

最新展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