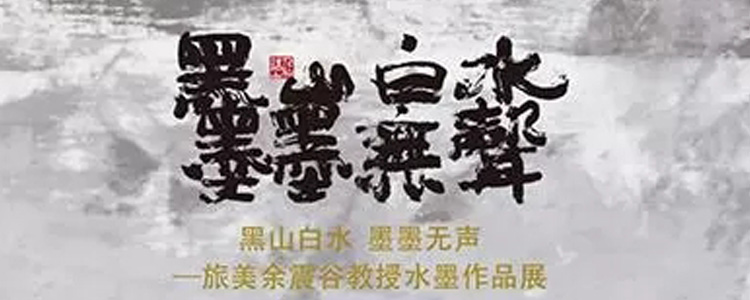
身即山川而取之
读余震谷教授作品有感
文/谢玮玲
中国山水画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人物、花鸟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三大艺术科目,不仅是世界艺术丛林中独特的风景,也承载着中国人文领域里最为深邃的寄托。受累于魏晋南北朝时局战乱动荡,许多失意的文人士子为避祸不得不归隐山林田园。寄情山水的生活不仅慰藉了文人士子空虚无奈的心灵,更是让山水画这种形式成为千年来中国士人抒情的重要载体。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山水画植根于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和归属感。而山水画创作伊始,反映的就不仅仅是图像与造型,更多是融入了诗性的审美和哲学的含义。从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到明代董其昌的“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再到石涛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理论,画家走进自然,体悟自然,最终将其内在的人文精神、气质、品格和审美境界融入在山水画中。其终极追求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境界不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山水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更加承载着“善”与“美”的哲学内涵。
但晚清以降,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当时内忧外困的中华帝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变得愈加激烈,也不可避免的将炮火引向了包括山水在内的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其后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艺术的发展更是停滞不前。进入1980年代,现代主义引入中国后,传统水墨艺术再次被当作僵化守旧的艺术形式遭到鞭挞和拷问。相比于当代艺术的其他门类,传统水墨艺术对于时代的反应显得迟缓无力,难以和当今主流的西方绘画语系和当代现实充分调和。如何将中国水墨艺术融入当代艺术范畴?如何在现代化艺术进程中延续传统笔墨和宣纸的生命力?这成为横亘在中国水墨艺术家们面前百年不得其解的难题。谷文达曾在他提出“观念水墨”之初,设定了他认为的“地界”:“一旦中国水墨艺术的创作逾越了此一界限,它将不再是中国水墨艺术了;但是,没有企及此一‘地界’的创作将不再是当代的。”正如朱朱在《灰色的狂欢节》中进一步的解读到:“水墨艺术本身在古代已然臻至难以企及的完美境地,如果今天的传统主义者仍然痴迷于笔墨,妄求于此种意义上的自成一家,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传统的复活有赖于新的媒介所进行的转化和运用。”
“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这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日夜照其影于素壁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身即山川而取之”的美学思想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他要求画者切勿拘泥于有形局限的思维之中,不要被尘世僵化的思想束缚住创作的心,更要走进自然,尽情体会本真之美,以此提升自己的绘画技艺和绘画理念。面对当代中国山水的局面,作为一位从小浸染中国传统文化又在西方艺术世界浸淫多年的美国绘画系教授,余震谷先生重新回到了山水画的立足点,将自己的选择面从传统的山水图案落实到了自我本身及所处的物质世界。“身即山川而取之”,他选择的破题方式正如他这次新展的题目一样,以最真实的生活为创作来源,充分运用身边的各种自然材料结合当代艺术理念,以“造山”的方式来重构他心中的诗意审美与处世哲学。
生活中常见的装午餐的牛皮纸袋,纸质类似于传统的中国皮纸,艺术家以娴熟的水墨皴法,使得大量类似岩石肌理的图案在人们平时所忽略的现成品材质上肆意表现。山水绘画技艺被巧妙的与当代文明生活的产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环保纸袋的颜色又恰巧如此地和自然中的泥石颜色相近,于是最终当有许多个午餐袋堆积“成山”时,观者获得了完全超越固有认识的感官体验,而艺术家对于现成品的利用更是将纸张来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的本质特性得以充分表达。
在另外几组阵列作品中,艺术家选择在中国传统的扇形、类似人脸的椭圆形,及蕴含哲学意味的圆形上,以美学中最基本的线条元素来描绘抽象的“不真实”的混沌世界,以此来拷问自己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并反思人定胜天思想的可怕。结合西方绘画抽象理念,将组成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基本元素万宗归一到最原始本质的线与面的关系,稀释、简化并重组,看似相同重复的表象却是由完全不同的细节所构成,这种宏观上的和谐统一与微观个体的大相径庭,形成了微妙的矛盾关系,恰恰映照出大千世界的存在法则,给予了观者超越视觉之上的意识感悟。更为巧妙的是,相较于传统山水画强调的留白,艺术家代之以抽象艺术的不确定性,试图模糊线面之间的边界,甚至是打破纸张作为作品的物质边界,将“留白”扩散到了画面外,给予观者更加广阔无限的解读空间。这或许是艺术家将传统山水画“三远”技法的朦胧再造,也再次将传统山水画意立在了当下。
传统中国水墨画背后所体现的是作者自身的心性修养,按余英时所言,这种心性修养不是单纯的自娱自乐或是自我升华,而是追求“道统”也即追求终极“理”法的体现。当古代士人寄情于山水时,其所展现的自然风景更是一种隐喻自我处境的符号,藉以此表达其内心批判的精神。正如高居翰在《隔江山色》中指出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那种“江岸望山”的构图并非抽象的反映元代山水画面,而是可以看成一种政治态度的审美表述。而在当下的表达环境中,无论以何种表象或形式呈现,像余震谷教授这样以作品承载内心深意,秉持万物有灵之恒道,问询生命本质的“造山”仍然值得尊敬,艺术也终将在其由“寄情”到“问道”的过程中,摆脱传统还是现代,东方或是西方,媒介与形式的桎梏,而升华至更为广袤无垠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