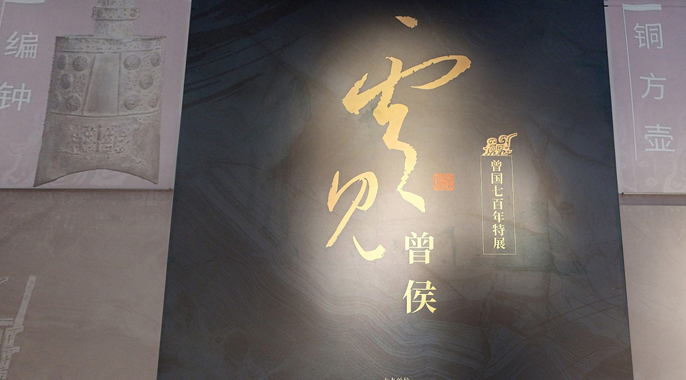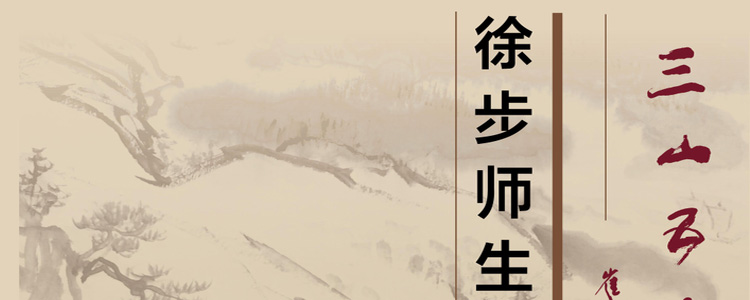
庐山者,结庐而隐居之山也。相传殷周之际,有匡俗兄弟七人好道修行,结庐于江西九江之“敷浅原”,时谓如“仙人之庐”,故称“庐山”。后世便以庐山为归隐之志所在,历代名士游历而吟咏庐山者不计其数,使庐山在自然风光之外,更增加了文化色彩,也使人们在幻境中意犹未尽。看庐山不如画庐山,画家喜画庐山当在情理之中。山水画发韧之初,就有宗炳“眷恋庐衡”,不忘庐山之游。五代荆浩深居太行山,却画出《匡庐图》。明代沈周未必到过庐山,也画出了《庐山高》。黄秋园虽在江西,也未登庐山,却常以《匡庐胜境》为图。张大千一生好游名山大川,居然未至庐山,然而去世前绝笔之作,竟然是巨幅山水画《庐山图》。由此可见,庐山作为归隐情怀象征,已臻人生理想境界,因而为历代画家所钟爱。
为了真切感受庐山胜景,实地一游很有必要,“三山五岳游”便是这一愿望所至。“第一山”去了黄山,“第二山”则为庐山。庐山之美,以清雄奇富为最。为了体现这一审美感受,在写生中便力求以个人情怀和画学修养,对现实景物进行取舍剪裁,加工改造,变异升华,甚至加入夸张和想象成分,使之成为“画”,呈现一种“笔墨行迹”,留存一段“烟霞胜境”,而非一个“现实版庐山”。古人不到庐山,却能画出庐山,说明山水画乃理想之境,不仅画眼中所见,更要画心中所想。所谓“胸中自有丘壑”,是以“胸中丘壑”驾驭“眼中丘壑”,然后变为“纸上丘壑”,即以我之心神,采天地之灵气,写生生之意象,便是山水画写生过程。能在生活中捕捉到活泼泼一股生气,且能迹化在宣纸上,便成了山水画写生作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早在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就已揭示出了艺术欣赏及创作“秘诀”,吾等游庐山方有所悟,山水画写生亦如此,身在庐山而又能跳出庐山,才能表现出“庐山真面目”。
徐步
时戊戌秋八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