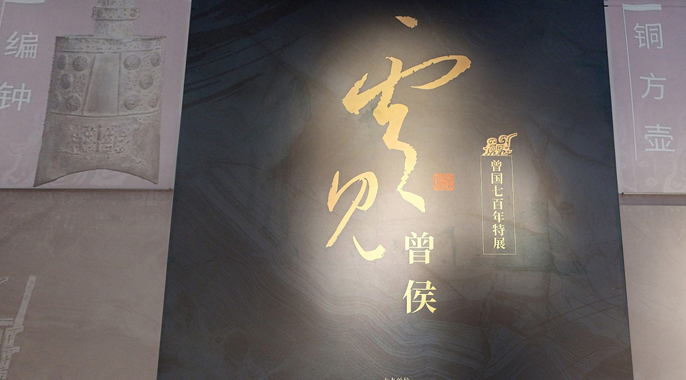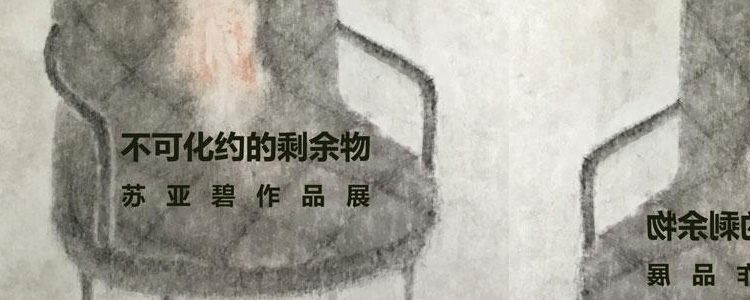
不可化约的剩余物
文:罗菲
苏亚碧自1998年从云艺毕业以来,一直将身边的日常什物作为绘画的对象:一把梳子、一枚别针、一把钥匙、一件衣物、一张床、一个抽屉……它们以轻盈的姿态游离,成为被捕捉、被凝视的对象。在过去二十年始终如一的专注里,苏亚碧从对日常什物状态的描绘发展为对日常生活本身的隐喻。
这些朴素的日常什物来自艺术家早年的生活现实——学生宿舍和家里简单的个人用品。那是一个生活尚未被商品及其品牌全面覆盖的年代,每件物品都与它的主人有着情感上的联系。艺术家却从描绘这些什物的过程中把握住了某种隐微的精神性力量——那种极易被抹杀也极易被滥用的内在品格——诗意。这种力量的真实性来自她作品中所投入的生活时间的痕迹和对日常生活的位移性陈述。
这些朴素的日常什物显然不是生活的重点,更不是目标,它们在苏亚碧二十多年的画作中,只是生活现实与绝对精神之间的某种剩余物,不可化约的部分。在商品与信息大量堆积的景观社会,身边的日常物常常遮蔽着本真生活,也遮蔽着这些物件的使用者。
苏亚碧通过不断描绘、塑造这些日常什物的游离状态,使其从日常生活空间中流放,获得进入诗意与精神的领域。苏亚碧的任务则是去捕捉那些日常什物被流放时刻的仪式感。在近期画作中,那些神秘的火焰、光晕和帷幕,让这种仪式感变得更加强烈。
尽管如此,这些形象同时也处于即将消散的神秘气氛中,仿佛随时都可能坠落,回到物质世界的关系中。苏亚碧的艺术也正是把握住了那种消瞬即逝的诗意中的人与物的关系,使它们偏移了自身所处的物质世界的位置。这也使得艺术实践变成一种可以让日常生活产生位移的陈述,从而让人发现日常生活中布满了诗意与神迹的瞬间。
这不断重复的对日常什物和生活在形象上的位移与流放,成为一种基于景观社会的抵抗,也是一种实践逃离的自由。这是苏亚碧的艺术区别于很多矫揉造作的浪漫的私密日记体艺术的地方,她在那些被流放的日常什物中捕获了一系列针对日常生活的反规训的隐喻。
2018年9月2日雨夜
昆明
柔性的现实寓言
文:薛滔
苏亚碧和我是初中同学,同在大理洱海边长大。在14岁的时候,我进入画室学习画画,从画几何体开始到后来上大学,再到以后的艺术家生涯,这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事。因为达芬奇也是在14岁的时候开始学画的。然而尽管如此,当我面对苏亚碧的时候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她比我早进入画室,而且她的画一直贴在墙上作为范画。13岁那年,我趴在画室窗口看到贴在墙的让我惊叹不已的素描作业就是她画的。虽然我年龄比她大,但进入画室后,苏亚碧是我师姐,而且后来我还知道米开朗基罗也是13岁开始学画的。这件事情一度成为我人生中的阴影,挥之不去。
在最初学画的那两年,超越苏亚碧几乎成了我在画室的奋斗目标。于是经过刻苦努力,终于在初三的时候,自认为就快要赶上她的时候,苏亚碧考上了云南艺术学院附中,进入更专业的环境学习。而我则在高中继续用课余时间来画画,这一下子便成了专业与非专业的天壤之别,让人非常沮丧。后来,才华出众的她附中毕业后保送进入艺术学院,而我也考上了大学可以进入专业院校进行学习,这才慢慢抹平了心中的遗憾,才可以正常的和师姐愉快的相处。
从开始进入画室至今,一晃就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当年的画室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从画室先后考上大学的兄弟姐妹数以千计,然而能够一直坚持画画的却寥寥无几。当年充满理想的艺术青年,大多都沉默于现实之中,而苏亚碧却一直不改初衷,选择了艺术家的道路,这让我觉得异常欣慰。很多当年的同学都已经天各一方,甚至同处一城却杳无音讯,而我与小苏因为共同坚持这犹如苦行般的艺术创作得以长期保持着联系,这是非常幸运的。在多年的坚持创作中,苏亚碧逐渐成为云南当代艺术的中坚力量,中国颇受瞩目的女性艺术家。她的作品从“记忆与日常”、“坚固与柔性”、“经验与伦理”等诸多方面,展现出女性艺术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
记忆通常是日常影像的储存与放大,有时是某种感受的长期存留。在苏亚碧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别针、梳子、毛刷、镜子等物品,显示了一种敏感性格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图像化处理,这是女性特有的敏锐与偏好。这种对于日常物件的选择性记忆,并没有还原一个真实的现实,相反却让我们对这些熟悉的物品产生陌生感。一种被记忆过滤后的,来自日常生活却疏离于生活的异样感受。苏亚碧通过对记忆图像的处理,呈现出一种真实与虚幻的特殊关系。存在或者是不存在的,真的或者不真实的,这种人类精神世界里特有的恍恍惚惚却又关于切身感受的微妙体验,被苏亚碧准确的表达出来。
除了绘画作品,苏亚碧也会用金属丝线制作一些作品。通常情况下艺术家并不在乎对于作品属性和种类的界定,而苏亚碧的这些作品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界定她用金属丝线编制的作品是装置还是软雕塑,那些观念与形式并存,功能与材料同在的作品,是一种介于两种类型之间的实验和探索。即便如此,这些编制作品还是延续她惯用的图像。镜子、梳子、裙子等等,女性特有的,象征柔性的视觉符号。然而,这些看似柔软的漂亮的金属丝线所呈现的柔性图像,实际上却是坚硬的,容易被刺伤的。金属丝线的坚硬与沉重,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漂亮和柔软,这种矛盾的并存,也许折射了中国现实中女性的特殊身份。与绘画中弱弱的对于身份的隐喻不同,金属编织则更像某种关于身份的宣言。
无论是绘画还是编织,苏亚碧的作品都有通过现实经验来挑战伦理的试探。不管是花虫蝶草、裙子别针,还是沙发、窗帘、床和桌子,生活物品的异化本质上是传统伦理的异化。在中国构建新世界的飞速发展中,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中国人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变得猝不及防。道德沦丧,传统价值观崩塌,既有伦理已经不足以支撑现实世界,新伦理却又更接近谎言,而人们不愿意放弃生活,在无所适从中,隐藏着对不知什么是往昔的留恋。一切都处于悬置中,既美丽又诡异。逐渐枯萎的传统亟需一套更新的伦理来适应和指导日常生活。于是,我们从苏亚碧的作品中,那些悬置的充满诗意的日常物品中,观察到一条正在触碰和议论伦理的暗河。来自个体的生活经验,试图诉说一个新秩序。这种来自生活经验所虚构出的伦理不是对过往和当下的注释和辩护,而是面向未来的寓言或试探。毕竟我们的肉身走得太快,精神已经崩塌而且逐渐与肉身分离,这种埋藏在现实经验中不易发觉的焦灼痛感,被苏亚碧用视觉形式不断的表现,经年累月小心翼翼锲而不舍。
对于职业艺术家来说,作品创作不仅仅只是工作,更多时候创作即是生活。大学毕业后的小苏,又回到洱海边生活和工作,她的生活与创作完全融为一体。虽然说她的作品中有日常经验参与,但在现实中作品与日常生活难以分别,其作品即是经验本身。她的作品不断的和现实进行纠缠,试图厘清这个如梦如幻的不实世界。正如大理的风花雪月对于游客来说犹如诗画般的梦境,而对于生长于斯的人们来说,他们深知下关狂风堪比无奈和残酷的社会现实。苏亚碧置身其中,用作品去把握那些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所有关于生活的局部和整体。既是赞美也是批判。因为但凡鲜活的生命都会对于社会有敏锐的感知,而艺术家尤其如此。
更多的时候,小苏的作品仍然是诗意的存在,以记忆的方式,优雅的表现着对现实的关怀。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日常诗意之外
文:乔丽丹
初读苏亚碧的作品是在2016年,认识她的作品要早于认识艺术家本人。那时见到的作品中,一张平置的板床上,斜放着一把老式床刷,画面波澜不惊,作品本身没有多余的语言,质感朴素,情绪冷静内敛。
苏亚碧与其他当代女性艺术家不同的是她比较少直接介入关于政治、性、伦理道德等尖锐的问题的谈论,但她又与大多数女性艺术家一样倾向于用日常中常见的情境、用品来入画。她的创作关注却又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经验表面,这种关注是她精神空间不断建构、完善、深刻的过程。与其他艺术家一样,美对于她的生活来说是需要的,但那些谄媚、轻薄、虚假的美对她来说又是不安定和无意义的。
苏亚碧以女性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镜子、梳子、别针、床刷、裙子、衣柜等事物作为画面元素,将这些事物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作为女性特定的生命体验式的符号。在画面的诗意以外,隐隐又能读出一些当代女性的精神生存状态。除此传统绘画方式以外,艺术家也在不断尝试其他材料,如用铁丝这种线性的材料以“缠绕”的方式进行创作,在繁缛缠绕的制作过程中艺术家得到了某种乐趣和满足,但这或许也是对女性在生活中扮演角色的无意识表达。
这次展览的作品与以往有所不同,晦涩的画面中隐藏着某种不安,不安的背后似乎随时会有某种不测紧随其后。封闭的画面中,半边拉开的窗帘,隐于其后的楼梯通向未知,窗子透进来的光被反复描摹的笔迹遮盖,晦暗虚无。占据画面主体的沙发,悬置的别针蕴藏着不可侵犯的力量,沙发靠背向上炸出的边缘,四脚纤细的椅子上燃烧的火团、沙发上点燃的火柴,晦暗的背后似乎总有某种不可控制的力量要将这平静摧毁。物象还是艺术家常用的,在不一样的情景中,这些日常寻常的事物带来了颠覆性的黑暗特质。
苏亚碧的生活一直是平淡无常的,大理带给她的安逸,在她看来美好的有些虚假。这种美好在她看来是被商业炒作或文艺青年无限憧憬美化后的假象,这般甜蜜的乌托邦在遭遇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堪转瞬又被打回原形,城市生活虚幻和现实的交替带给她的便是不安。但苏亚碧又时及其克制的,绘画的过程对于她而言更像是修行自疗的过程,在此之间她会将痛苦、纠结的情绪消解,使得画面最终归于平静。她的作品不是感官直觉的本能显现,作品的背后隐藏着艺术家对社会、生命、人性等问题的思考。这种经过艺术家私密的感悟消化后的语言,也就更为深刻了。
2018年10月
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