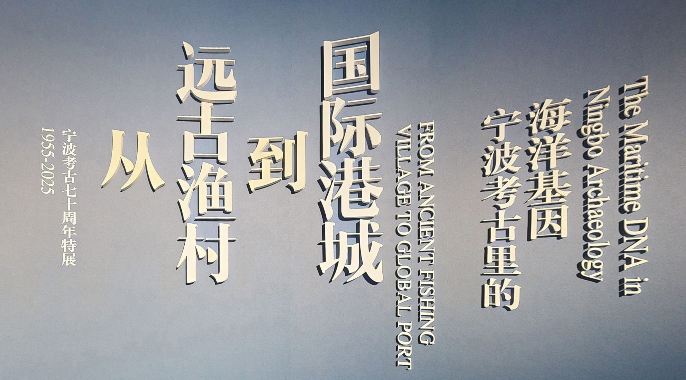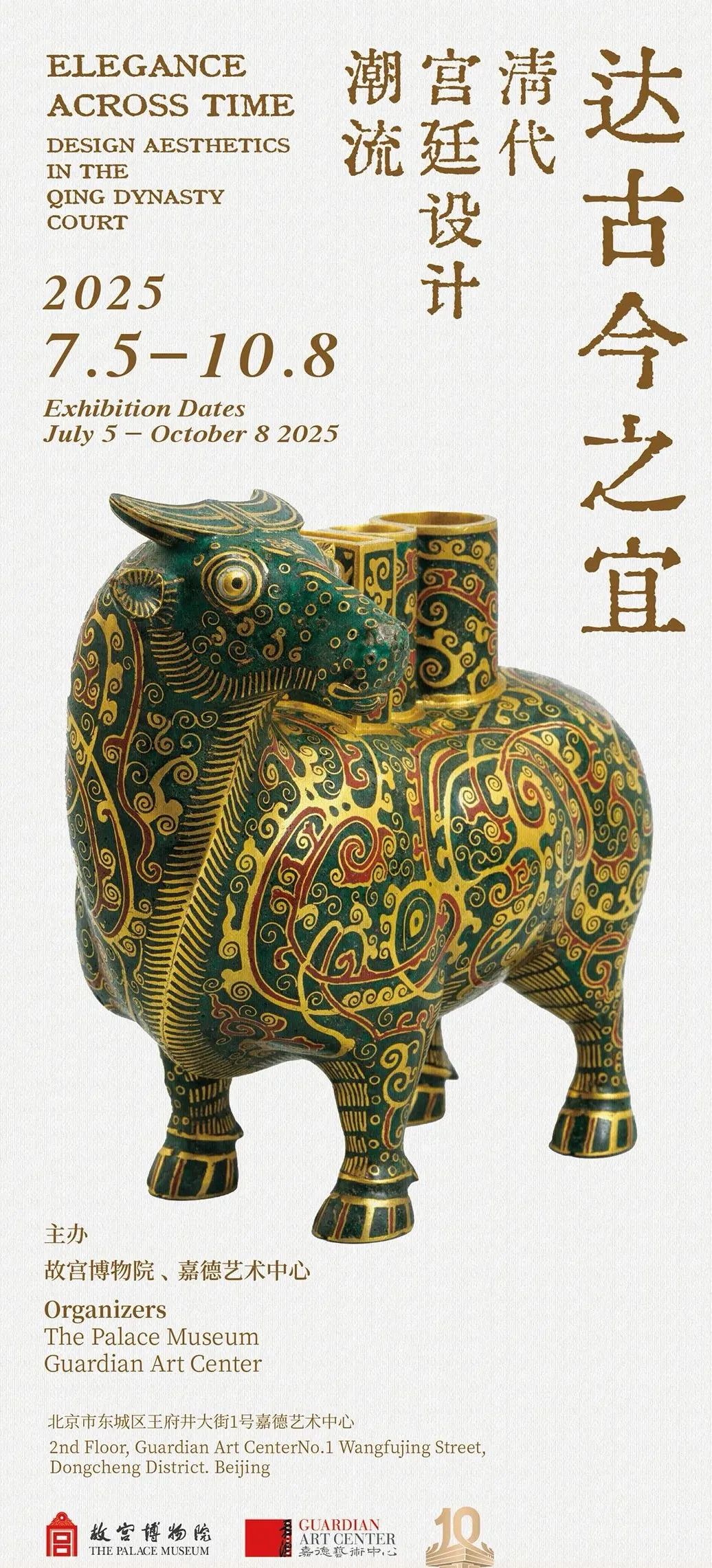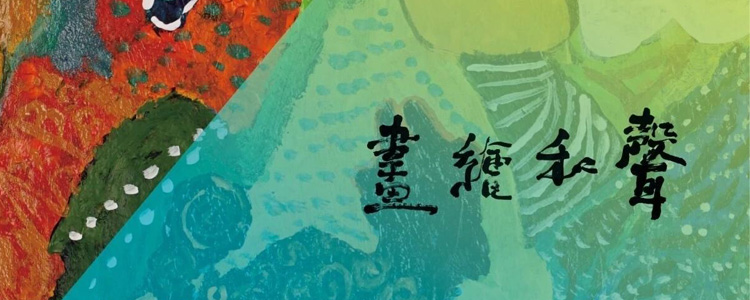
牧羊人摩西问上帝姓甚名谁,上帝回答说:“我就是我”……
吴声和绘画相当于梦境,玄妙的是他既没有学习绘画还茫然于梦境——他在深沉的梦中,自己就是宇宙,就是神祗;他在绘画虚无中进行创造,其创造成了首要的虚无。从而,孕育了艺术雏形而后又产生了具体绘画的深渊,这种绘画指向艺术,但却毫无内容,算不上精神表现的直接方式,却是本性显现和灵魂密码的一种用途。如果他这个有关绘画的传说故事富于传奇色彩,交织着艺术价值的真实和难免的谬误,并不感到奇怪这句托辞还是让人们在达成共识的脆弱上依然分崩离析——或许从现在起,他的躯体已不属于他,而整个艺术力量却倾向了他——艺术正是人类世世代代具有的一场结束不了的令人困惑的梦……
吳声和绘画的突然性和天然的纯粹状态,以自我和他者的惊愕及淡漠,让它使人感到的不真实开始让绘画出现了漏洞。因由他不知艺术是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并且对于其
自身,对于天然神性,他始终如一的无法理解——特殊意义是本相的显现,天意就在其后,命运是惟一的实际之物一一领悟这个道理的人在行动时就能意识到这远不止是一种“绘画”或一个回答“我就是我”……
吴声和绘画的效用,在于规避了“愚蠢迷惑他终身”的宿命,和地狱形式作为永恆状态的人生轨迹,这也许是因为他知道疯狂正在前面等待着他。在他的所有绘画中,他以对绘画极度无碍的方式想象了一个绘画生态以外的家族,其成员全部有一种微不足道的但却是永不滿足的欲望:它们只用原色,只有补色关系;它们无法与同类对话,因为脑洞的差异改变了语言,说不通也看不懂,传统记忆无法让它们对接。可以设想,吴声和幻想这种由无知浇灌起来的恐怖,是因为他从未面对过它从而恐惧它,或许也是为了使用天道来驱散一生中曾经积攒的过多的自负与无聊。他也会以绘画为由夸夸其谈自己的艺术心得,尽管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对幸运的本性或失意的审美作出的令人欢欣的赞赏,他的这种思想不仅贯穿在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中,还体现在他为数不多的夸张艳丽的图画中。一张画就是一场对话,一种形式关系:在对话中,交谈者并非他说话的风格,他可以无言而尽显机智,也可以说出聪明世俗的见解而表露出愚蠢笨拙。总之,吴声和那种平淡而溫情的说教式风格与他的恣色璀璨依然混为了一谈——社会化会让一个人风姿卓越,艺术与真知灼见却犹如一个伟大帝国的废墟。然而,人世间没有什么比他对绘画的跳空高开來得更加突如其来并匪夷所思了。
作为一个绘画的艺术家,相对于社会来说就象是一个病人,像一个被人无视的人一样,艺术都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所以,绘画艺术家应当异常清楚,从根本上说,自己就是另外一个东西。这另一个东西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象艺术无法解释一祥,它袒露的就是未知——即不知道……
如果吴声和不再知道“我就是我”的时候,如果他羞涩于谈吐自己绘画进步的奇异时,并以知识量来驾驭自己的天性,是否就会体验到了一种解放的滋味——在绘画艺术的茫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