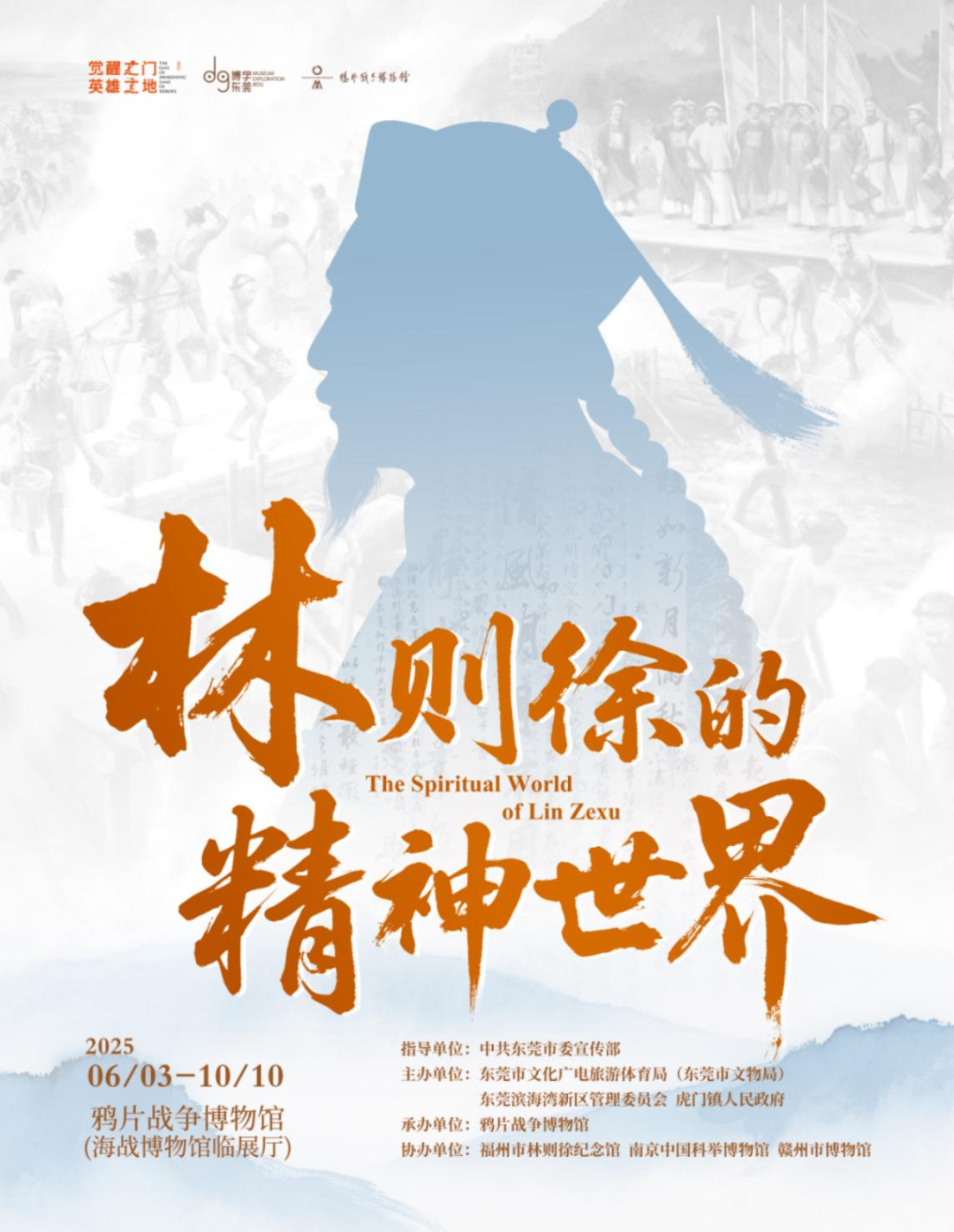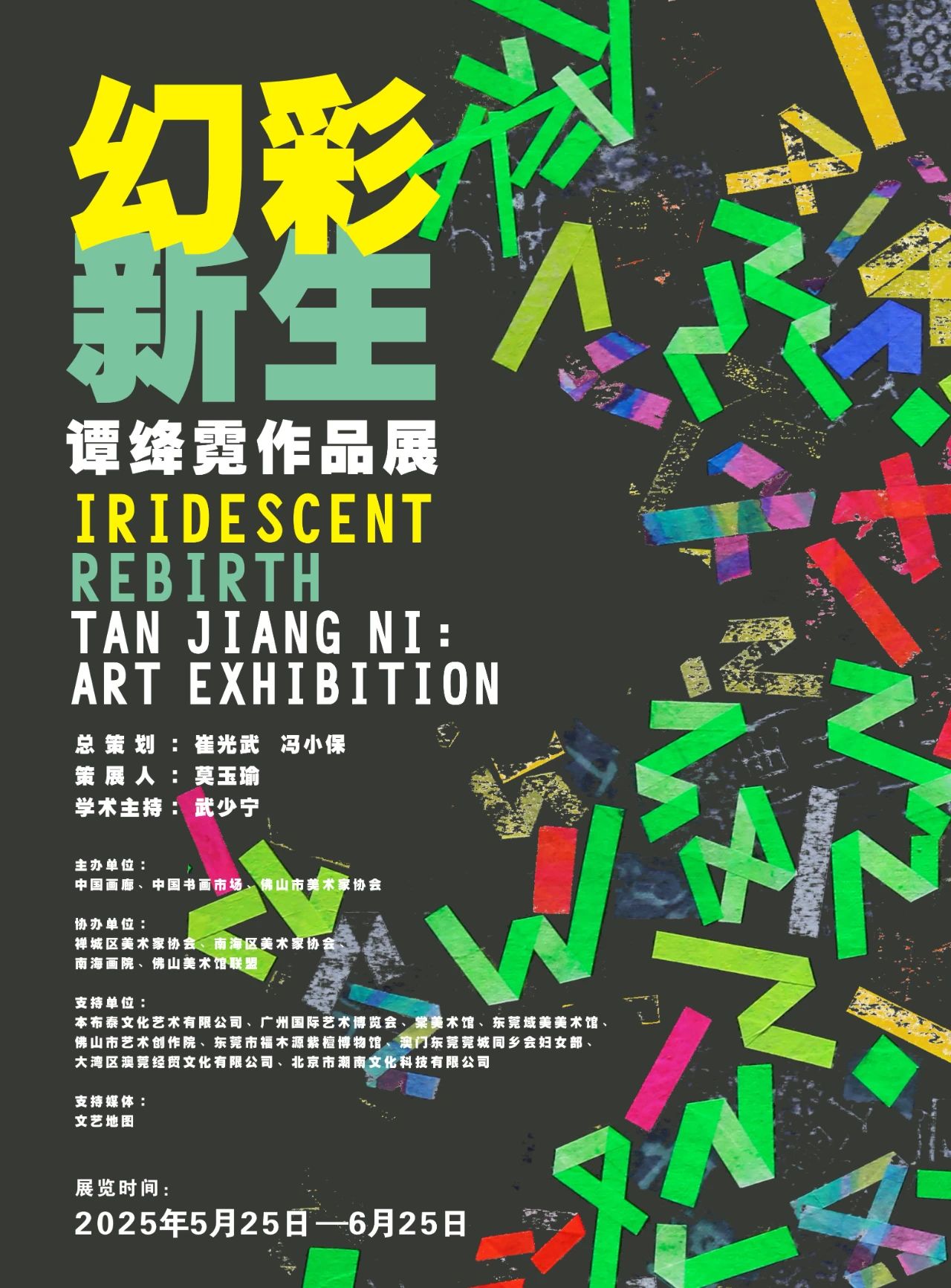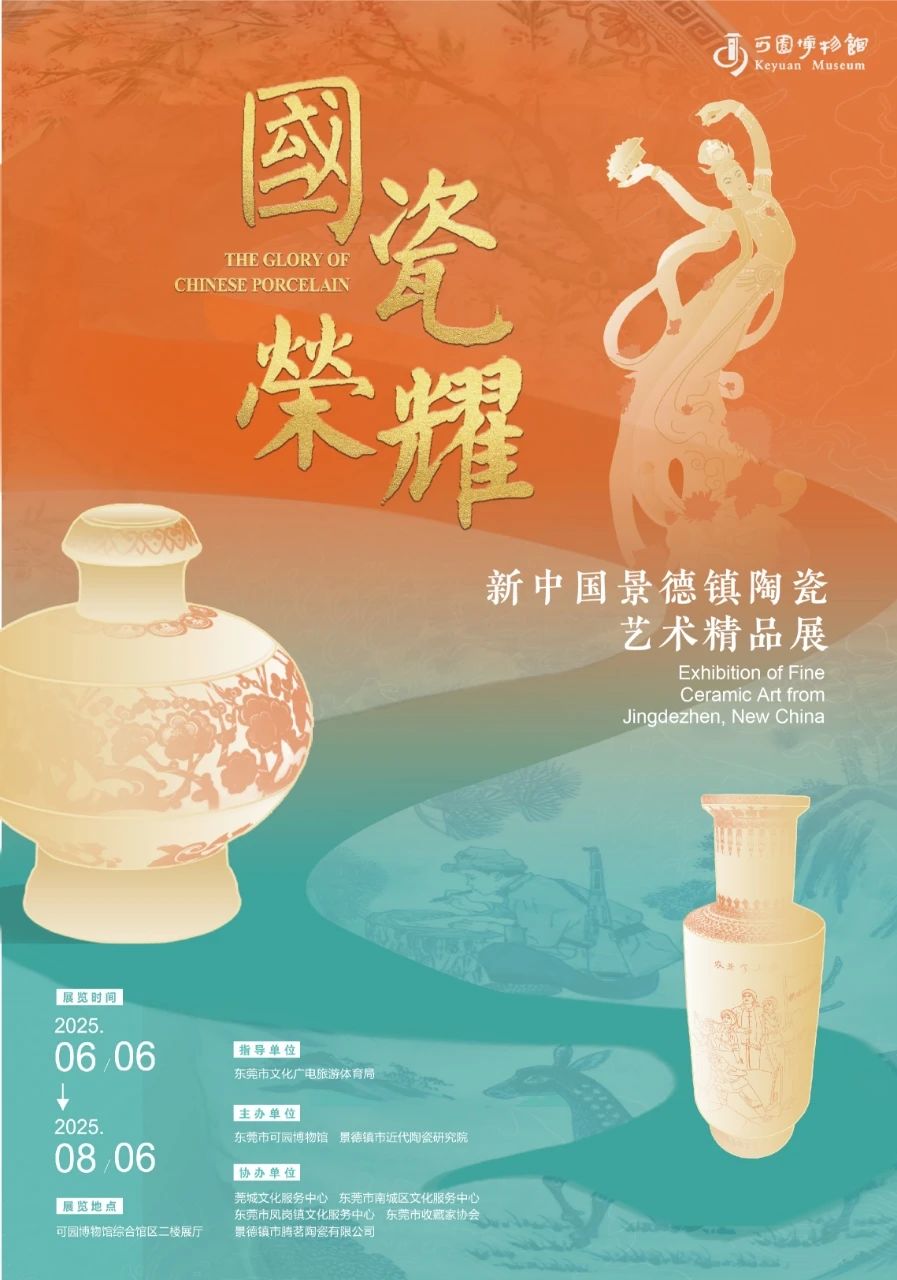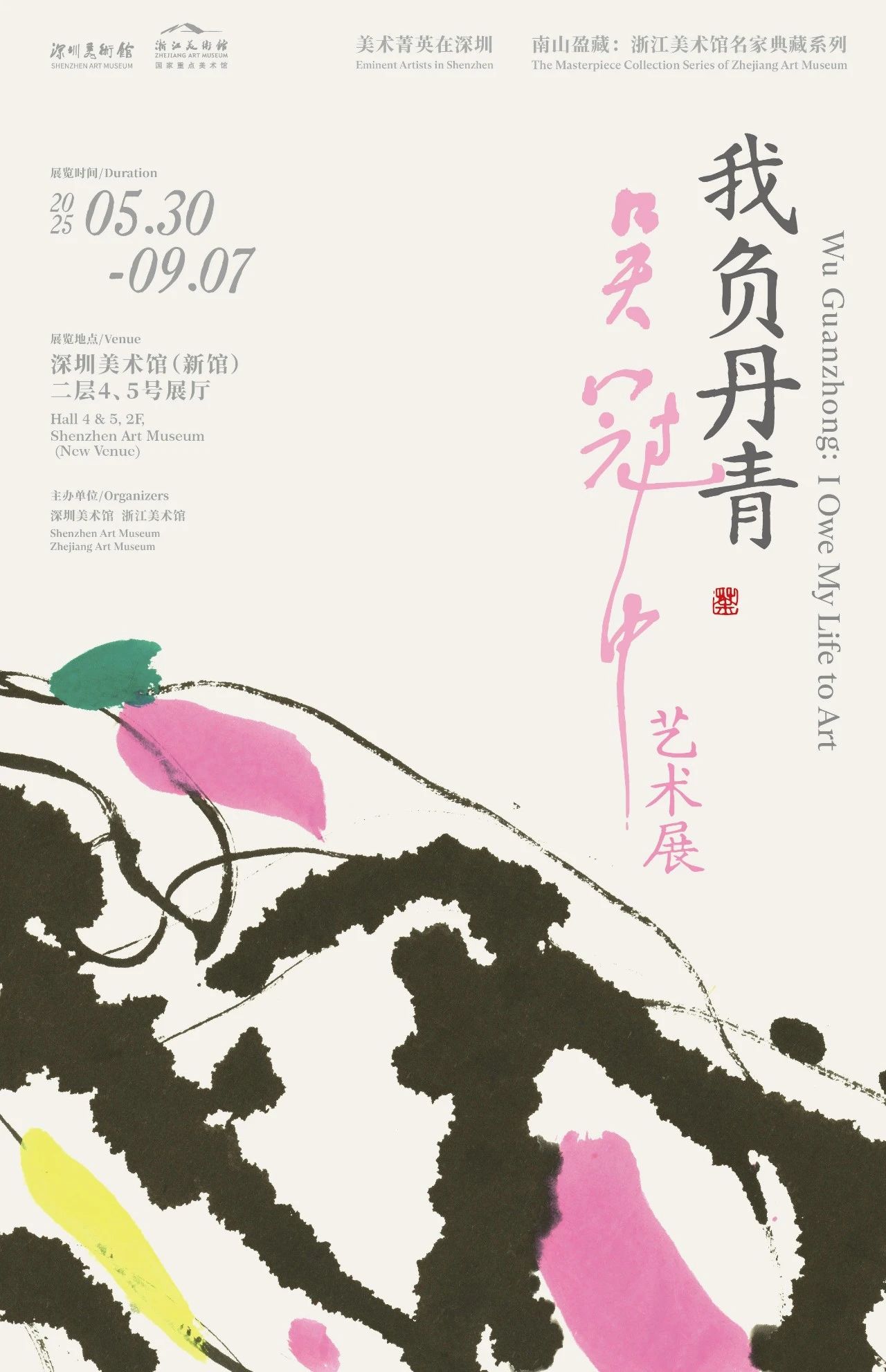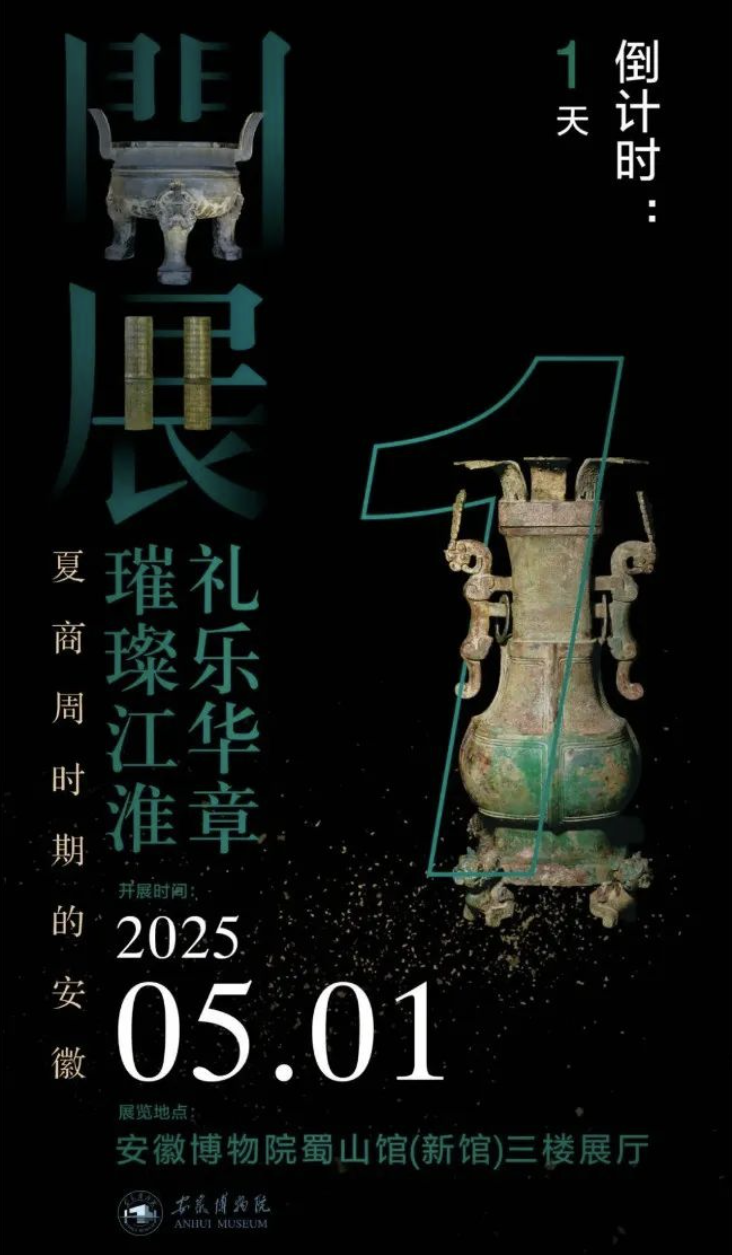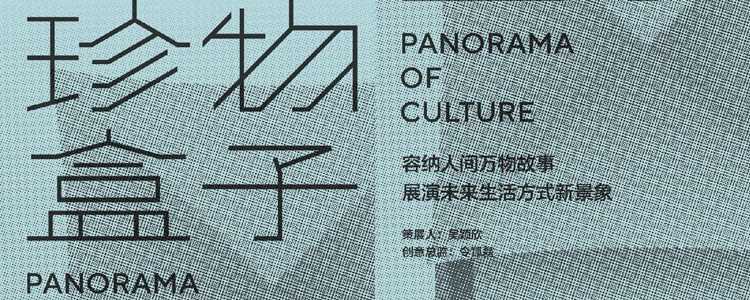
珍物盒子:从个人的文艺复兴景象出发
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值得每个当代中国文艺界人士憧憬的词语。
有如是荷兰的学者约翰·赫伊津哈说:“在听到‘文艺复兴’这个词时,迷恋过去的美丽的梦想家看到的是紫色和金色。”
我们透过这个以头文字R开始的词(Renaissance)透视出去,会看到些什么?是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广场,是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里的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还是明代的家具和摆放着澄心堂纸的书房?
“文艺复兴”这个词有着:“个人主义”与“现代性”的两层寓意。它如同阳光穿透了中世纪笼罩在人身上的迷雾,有如再生的神话,让人得以找到自己独立精神的个体——这样的人,才是具备现代性人文主义的人。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个人的命运跌宕的过程所感染,被人物当下的故事的烟霞所笼罩,在同时代,我们无法客观和准确地评判一个人,正如我们无法评判当下我们处于文艺复兴的哪一个阶段,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文艺的一些“景象”。
我理解的“景象”更在于一种抽象的意境,一种气象。它未必全部来自眼睛所见,而可能是一种对气息的感受力,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
我们在探索一种可能,有没有可能从个体的人生历程出发,通过他对自身最珍贵之物及其所经历的时代回忆。在2014年时,我和时在《生活月刊》的夏楠、张泉和马岭等编辑团队决心要完成一个不可能的项目。
我们决意这个项目需要覆盖20个文化的领域,每个领域限定4-6个人,通过选取100个案,以这个策划,或者说是一份调查问卷,在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人生故事、创作源泉的同时,我们也得以从一个侧面去观看当代中国的文艺景象,而这期《生活》就名为《文艺景象100》。在短短2个月内,完成了百余人的采访、联系工作,我们以让自己的都惊讶的编辑强度和速度完成了。这期杂志出街后,我们也在广州方所以及上海新天地举行了两个由内容衍生的展览,参观者众,杂志也一售而空。
杂志之后,在基于这组文字内容的基础上,由资深编辑陈飞雪等人花费了3年多时间再编辑整理的《珍物》一书在2017年推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珍物》一书屡屡进入了2017年年度的好书奖,也再次掀起了阅读“珍物”的热潮和广泛的讨论。
2018年,我们决定将“珍物”发展为“珍物盒子”,邀请更多创作人加入,我们也赋予珍物一个容纳万物故事的载体:盒子,珍宝之盒。而在这里我们以覆盖更多城市的巡展开始,意图展演的是一个未来生活方式的新景象。第一站,便是我们的中华文明的原点:古都西安。
这里所呈现的“珍物”,无论是物质或是记忆,我相信,一股文艺同心的精神,将由此潺涓汇流。而厚爱尊重,相互扶持,激发新能量,让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在各自的领域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这便是文艺复兴的生生景象,至于是不是文艺的巅峰,就有待后世的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