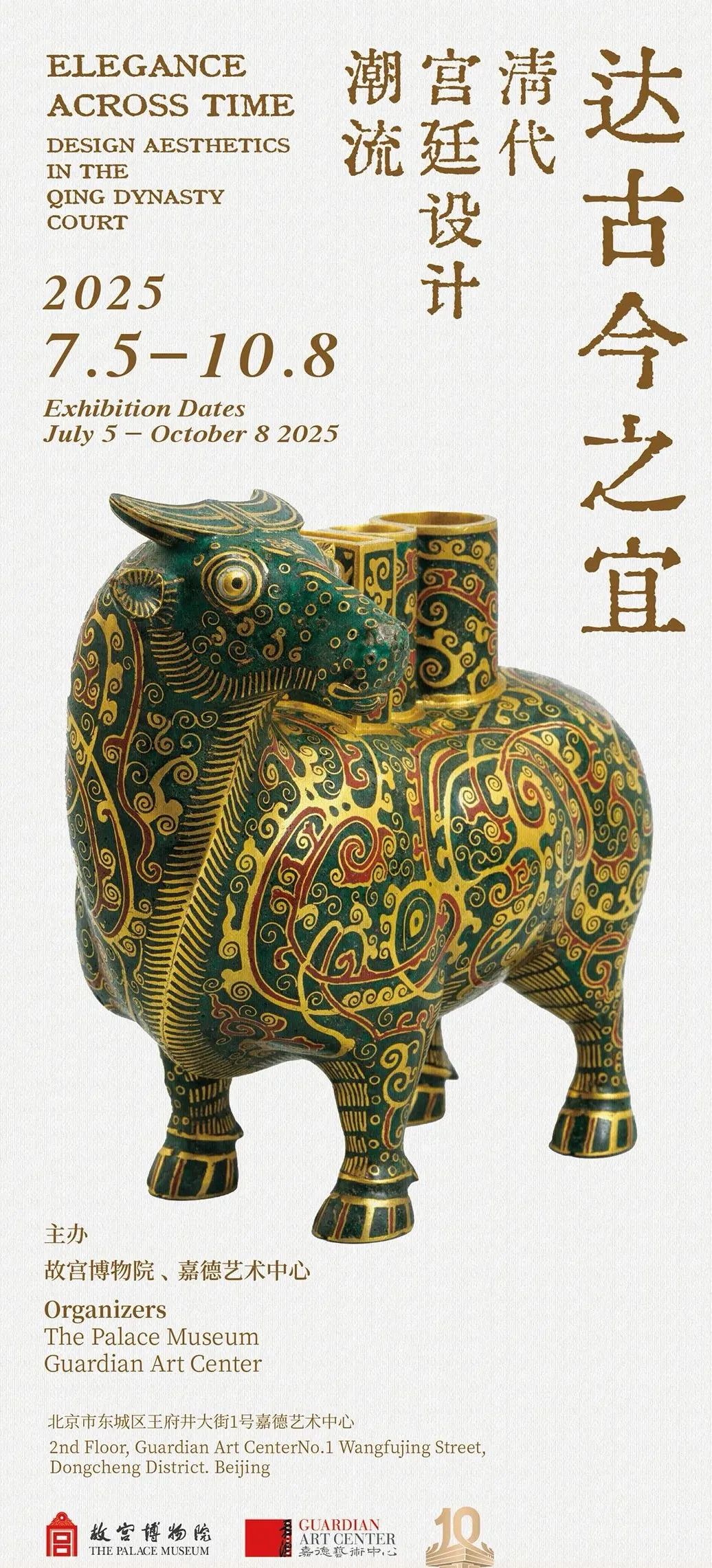一个自我暴露的傻瓜,把思考、感情、幻想留在纸上,纸是一座桥梁,它通向不可知的境界,钻到每一双与它产生共鸣和想象的眼睛,走向一个无极的世界,说是虚无吗?它存在于一种不可捉摸的幻觉之中,却确实在那里飞翔着、痛苦着、冥想着,说它存在,可我们的手却抓不到它,甚至碰不到它的衣角,可是我们被召唤着、激动着,在看不见的空间里打开了我们的思维,解放了我们的本能,恢复了我们的天性,使灵魂有了确切的位置,使死亡有了解脱,使痛苦得到了治疗。
——毛旭辉 1985年6月13日
当代就是今天活的一代人要活下去,怎么活下去的问题。生活将更美好吗?在20世纪,在两次大战期间,在战后的冷战对峙期,在中国的“文革”,人生大如噩梦,20世纪有过这么多的痛苦,当代又能怎么样呢?
当代要把人们带到哪里去?当代的诺言、神话一个个在撤除,一个个时髦匆匆来到又匆匆离去,当代没有给人一个确定的价值观念,确定了的是古代,伟大的古代,那是经过战与火,漫漫岁月的历史,给予它的子孙许多有益的确定的观念。
——毛旭辉 1996年11月
一个东西,某种事物只有从我们的生活中、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内心的关注。
一个人离去了,一块土地消失了,一间房撤除了,一棵树被砍到了,一种精神崩溃了,一种信仰瓦解了,一条河干涸了,一段生命的历程过去了。
当这些东西消失的时候,人们才会深刻地想到什么。人都是在什么之后才想到什么——这就是人的存在,人的宿命。
——毛旭辉 1996年11月
权力不是被限定死的,而是不知其所在又无处不在,它充斥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使社会集团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竞争”都只不过变成了政治纷争的表现,变成了预先安排好的,在整体力量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的场所……在资本世界里,到处都是市场,一切事物——包括所有的人在内——都被变成了“被利己的需要和大吹大擂的推销束缚着的,可以转让和出售的东西”。
——毛旭辉 1993年7月6日摘抄“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