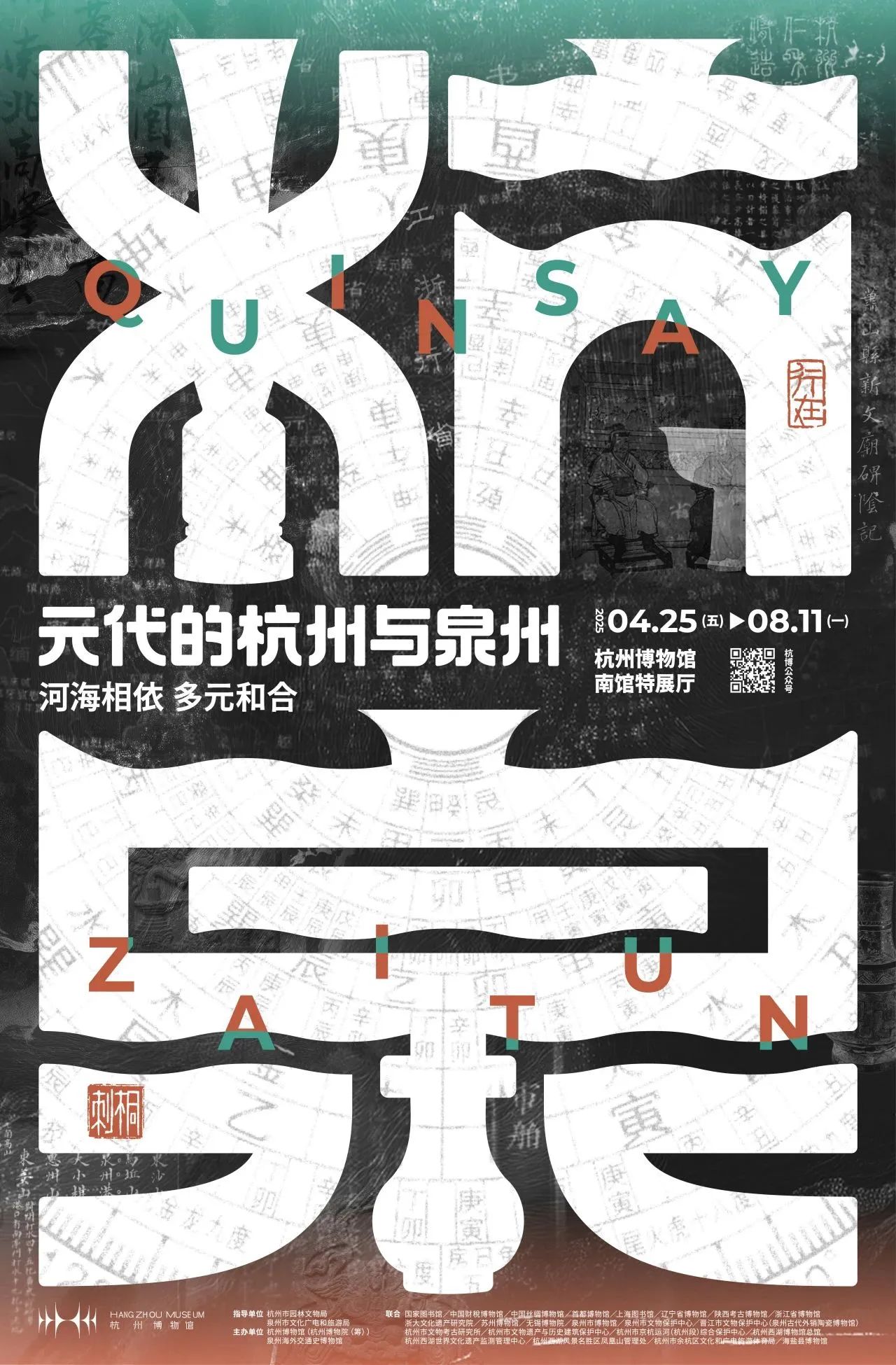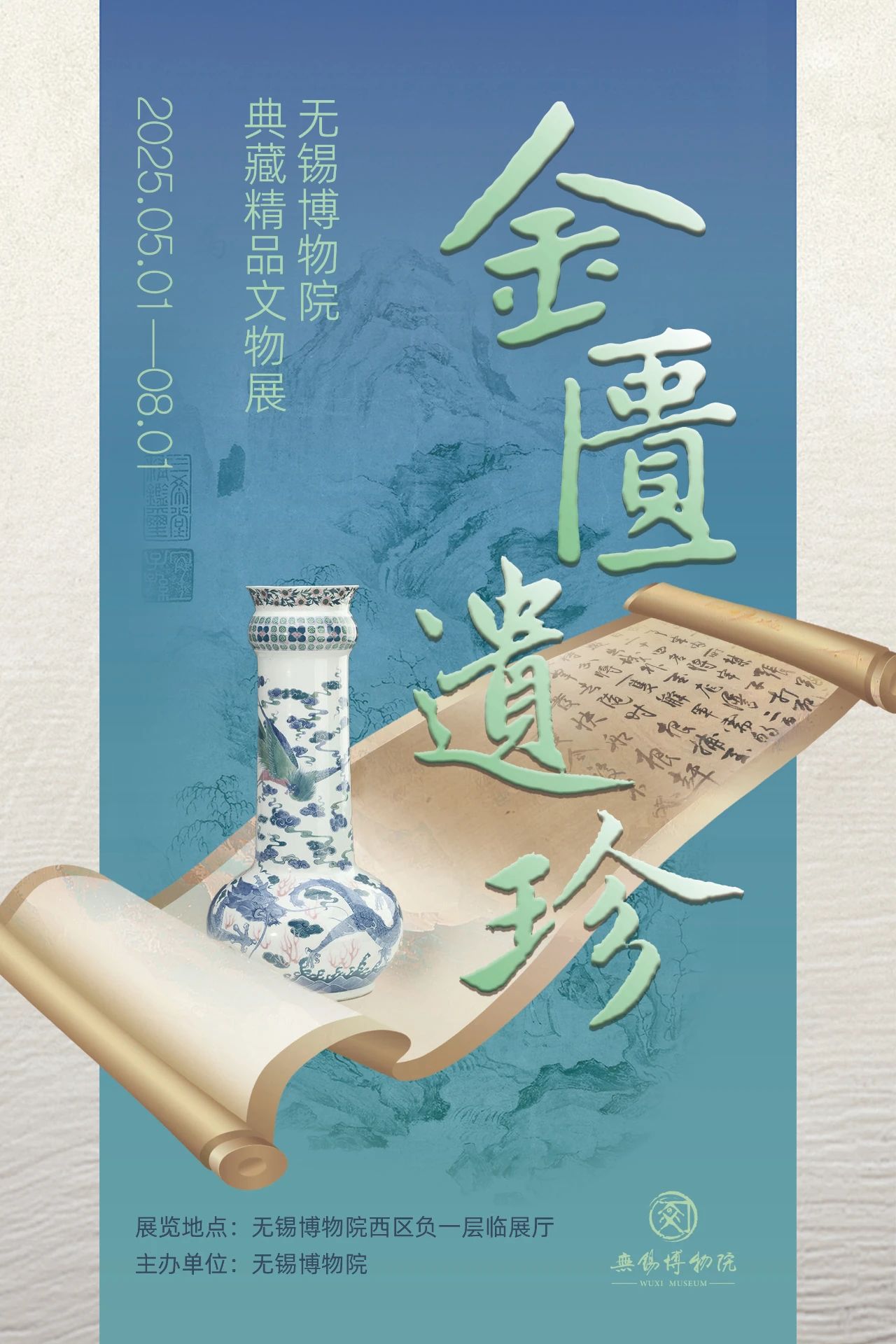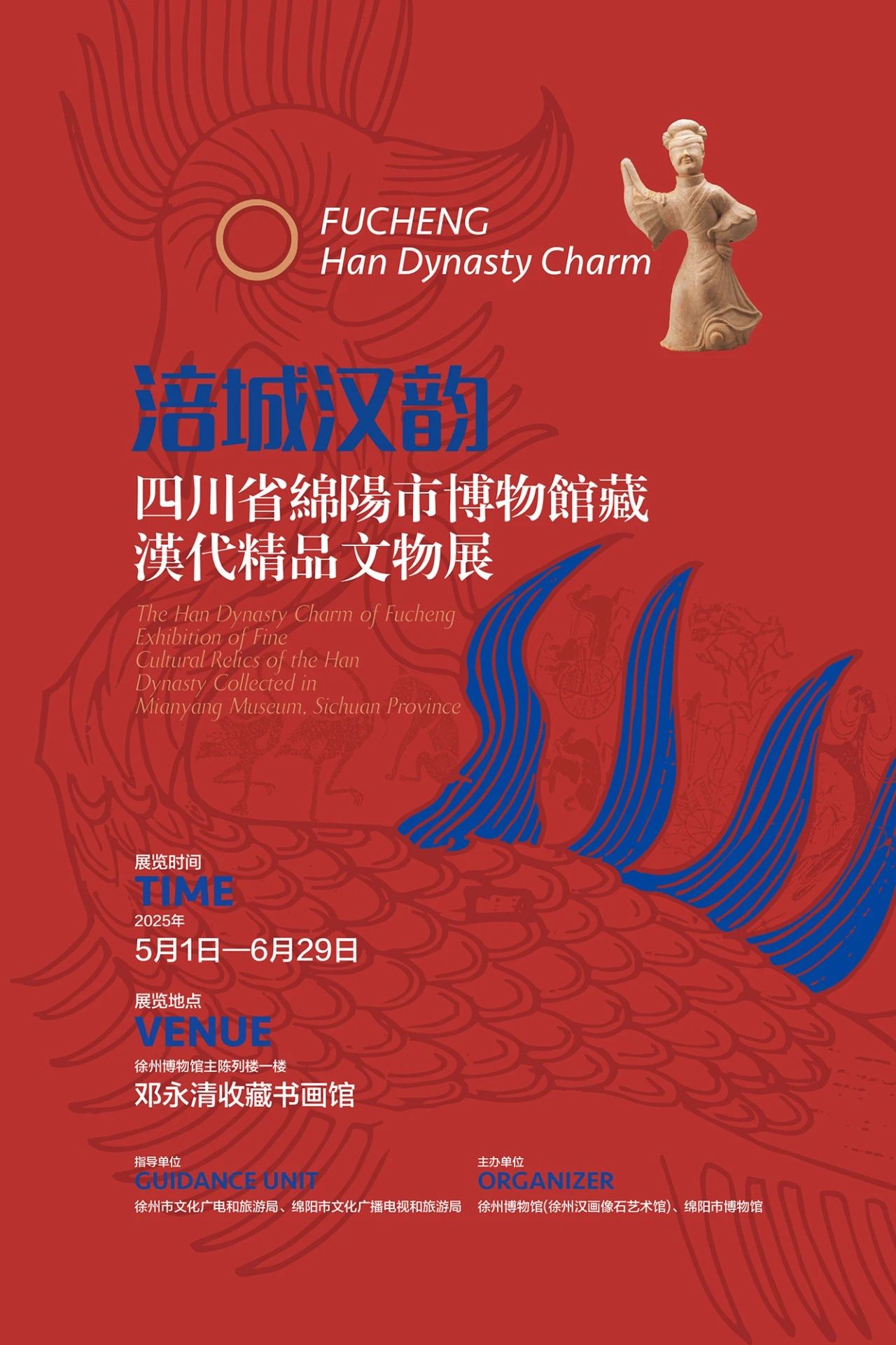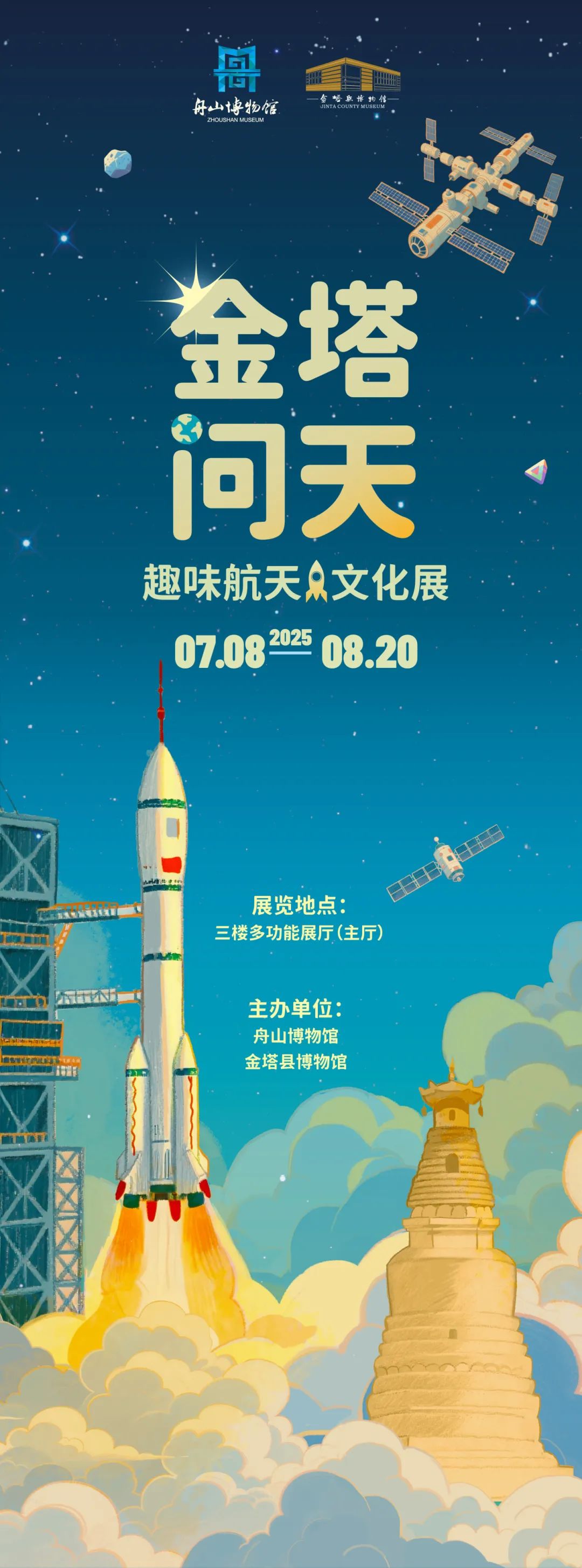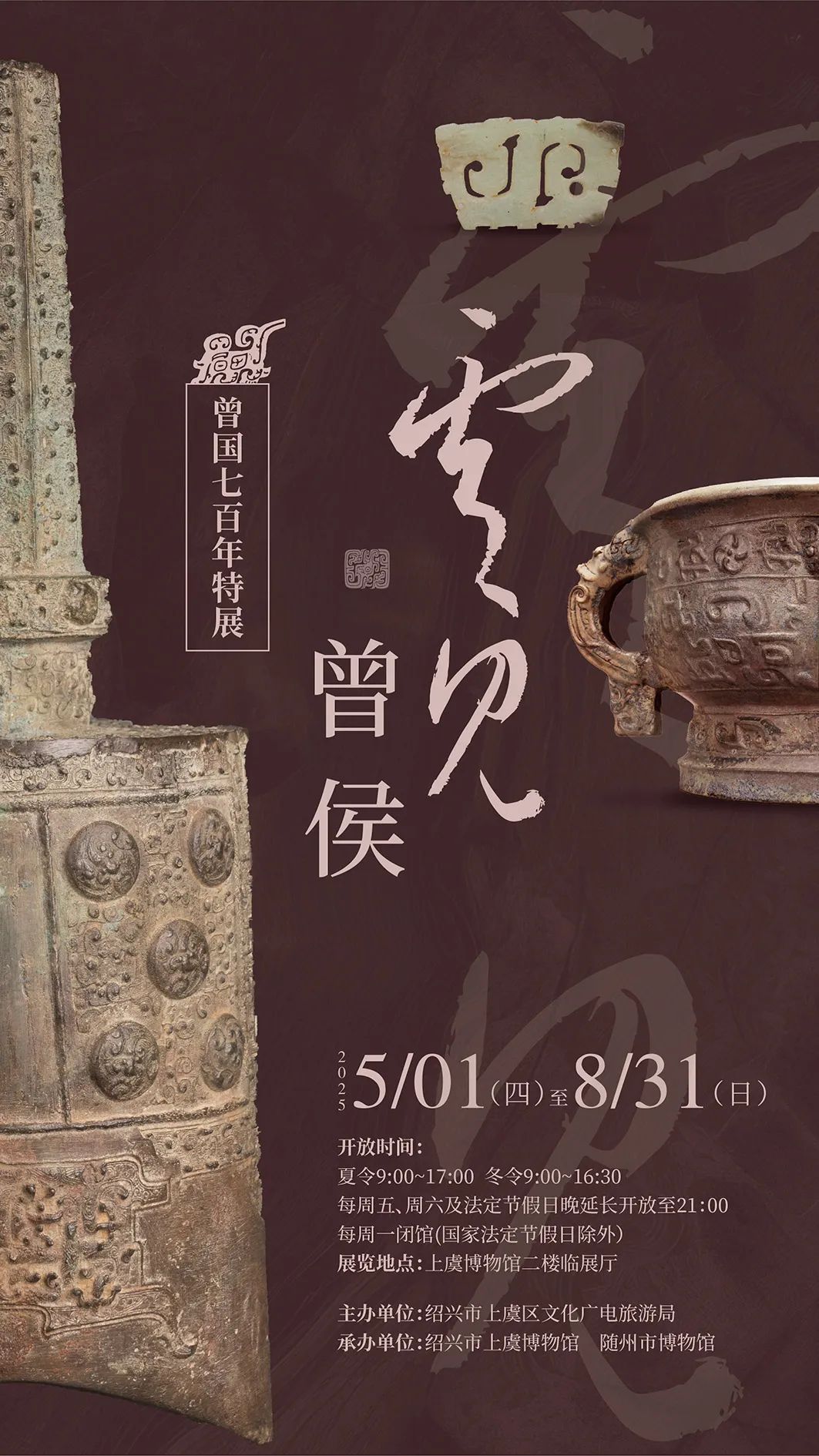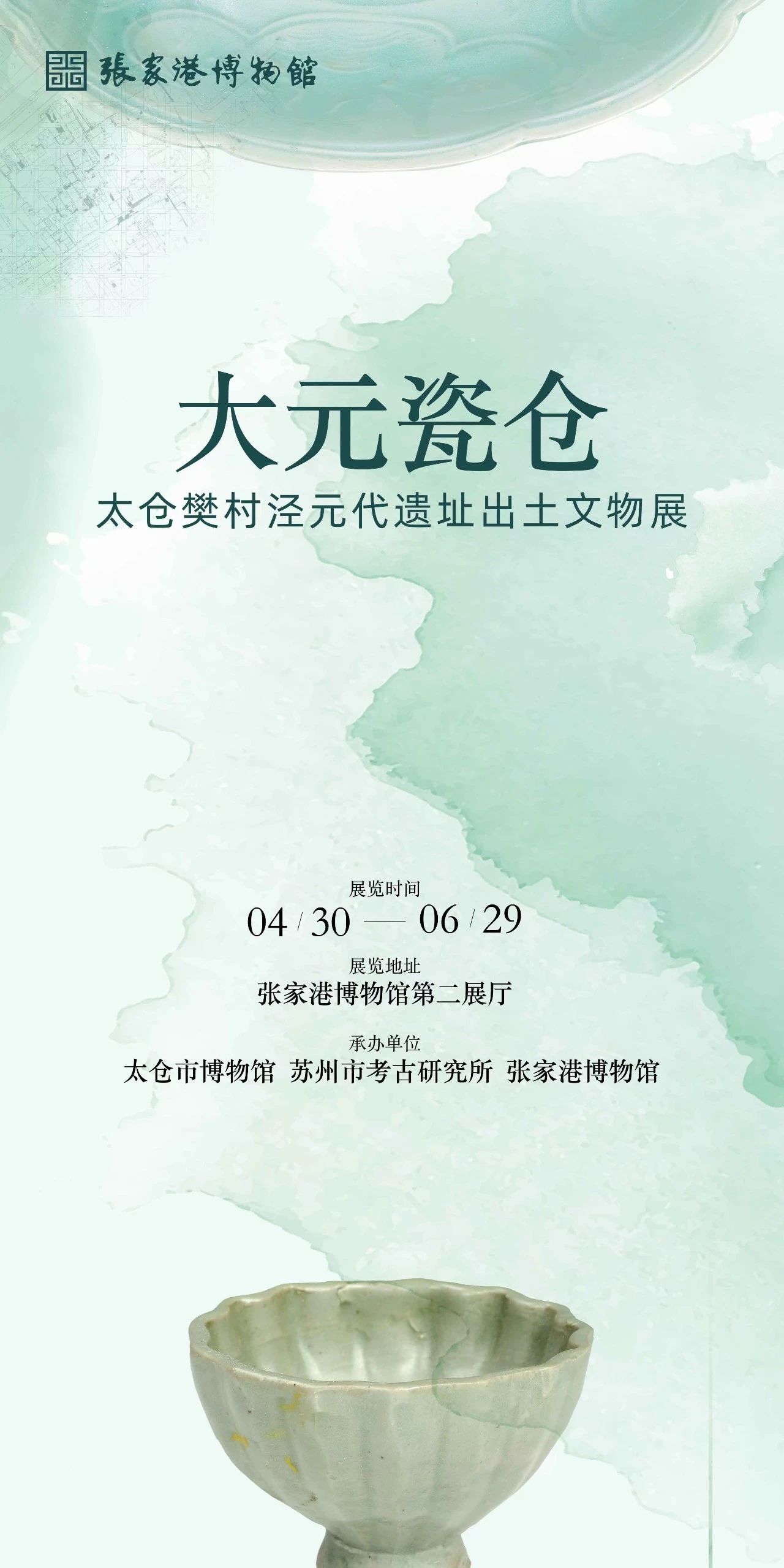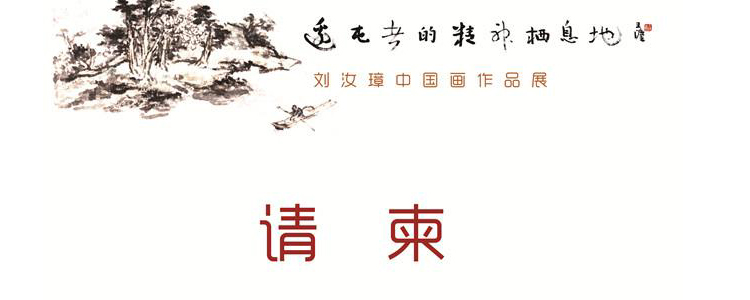
边屯者的精神栖息地
——谈刘汝璋的山水画创作
汤海涛(云南艺术学院教授 云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上个世纪90年代,在某次云南省美术展览中得见刘汝璋大幅山水作品,画面笔墨酣畅,气势汪洋恣肆,自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在其他场合读到刘汝璋的山水画,也曾经试图由画及人,从理论学习者和工作者角度,将其放在云南中国画格局当中做些思考和比较。2014年,笔者为“七彩云南——中国美术作品展”写作论文 《形式的侧翼——云南美术现象的发生及其文化效应》时,在云南山水画领域提及刘汝璋理所应当,另外一方面也源自当年读画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笔者就读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时,并不知道同学刘晓翔就是刘汝璋的哲嗣。当年刘晓翔是中师背景,我是往届身份。平日里,中师一拨同学有个小圈子,虽是同学,交往不多。加之刘晓翔低调,从来没有提及父亲的绘画创作。直到写作《形》文时,才隐约知晓了他们父子关系。现下和刘晓翔联系亦少,拜访这位令人尊敬的老艺术家的打算也没有和晓翔说起。恰好晓翔因父亲的展览,特意打了电话,送来之前出版的画册提供参考,希望我为他父亲写点文字,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了。
从中国画创作的格局而言,云南特殊且丰富的题材为花鸟画创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资源,加之王晋元、袁晓岑的砥砺探索,云南花鸟画创作可谓一枝独秀。而人物画有虽有梅肖青、张志平等代表性画家,但创作力量和梯队尚待加强,亦有发展的空间。而山水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无疑是云南中国画创作中的短板。尽管如此,云南依然有一批对山水画创作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的老中青画家。其中,刘汝璋就是云南山水画语言地方化探索的先行者之一。所以,借《边屯者的精神栖息地——谈刘汝璋的山水画创作》的写作,加深对云南山水画创作的认识,可谓一举两得。
简单地说,山水画创作完成了写生性语言向程式化语言转换后,所谓的树法、水法、皴法成为一种符号化表述,从而中国山水画转向了对技法的迷恋,同时彻底脱离了对自然造化的研究。由江南丘陵地带而来的视觉经验,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人画家的重复呈现,甚至成为了中国审美的一种特定的模式。正如郭熙在《山水训》中所言“生于吴越者,写东南之耸瘦;居咸秦者,貌关陇之壮浪。”一个地域文化就有特定的审美情趣。随着时代的发展,山水画不再是自然的再现,而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的栖息地。在审美价值取向的视野中,代表特定趣味的山水画样式的不断重复,就是对自己生存况味的一再体认。而地理地貌极为多样的云南,由中原而来的山水画创作的语言体系和审美系统,就面临着转型的问题——而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成为云南山水画创作者无法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正所谓:“学范宽者,乏营丘之秀媚;师王维者,缺关仝之风骨。”(郭熙,《山水训》)而蕴藉中原和江南文化的山水笔墨语言系统,在云南这个特殊的地域里彻底失效。所以,云南画家通常自知或不自知地面对如下吊诡:坚守传统,无奈文脉杳渺;探索创新,可惜画风不继。无论是花鸟画还是人物画,都没有山水画如此这般地给云南画家造成困扰。而在笔者看来,恰恰是以刘汝璋为代表的画家探索了云南山水画创作多重突围过程中的一条新路。
翻开《艺术的边屯者——刘汝璋作品集》[ 刘汝璋 艺术的边屯者——刘汝璋作品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 2011年.],边屯者三个字一直在笔者构思文章的过程中挥之不去。从略有质疑到若有所悟,到借用且转换了语境作为标题的关键词出现,确是刘汝璋山水画创作的特殊性所致。
再读刘汝璋的山水画,自然比二十多年前初看作品多了许多感受。画幅大是当下山水画创作的一个特点,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确不多见。本身尺幅大小并不关乎艺术作品的高下,但就画面控制而言,难度无疑提高。所以,刘汝璋从创作伊始,就针对画幅做探索难能可贵。其次,刘汝璋画面气与势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气通透、势畅达。一边半角的山水技法,无法表现云南山水的多样,而以全景取之,又无法表现云南山水壮阔的万一。所以,在画面上,气与势的平衡,出岫烟云的表现,安顿身心,让山水画成为自己的精神栖息地,想必就是刘汝璋的追求吧。
而对边屯者的身份,意味着在原乡和他乡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张力:渐次模糊的记忆恰是过往的来路,而历历在目的景物又是未来的归宿。可以想见,作为边屯者的结局无非有三:不甘者试图落叶归根,坦然者定然悠游异乡,纠结者肯定进退失据。有意思的是,这种持续的张力,恰恰有对应着云南山水画创作的困局。在笔者看来,刘汝璋就是一个坦然的边屯者,悠游在山水画创作的领域里,而山水画就是他精神的栖息地。段锡在《举步山水间——刘汝璋的山水画》一文中,记叙了刘汝璋山水画创作的一个细节:“由于条件限制,刘汝璋没有机会游历名山大川,但是他生长在小凉山脚下,全县的山头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那原始古朴的木板房,炊烟缭绕的小山村,身负荆棘丛林的悬崖峭壁,如鸣佩环的山间瀑流,川流不息的占河、金沙江,马帮走过的林间小道……无一不激起他胸中创作的波澜,成为入画的最好题材。”[ 段锡 举步山水间——刘汝璋的中国画 云南日报 1996年3月7日.]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刘汝璋在中国山水画创作中,就是一个典型的边屯者。他关心的就是古人关心的问题:“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自适,纵烟霞而独往。……不知画者,难可与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所以,永胜一隅之地,其山其水,就是刘汝璋的精神栖息地。
而正是刘汝璋山水画创作对一隅之地的关注,将笔墨与对象,将物像和情感结合起来,拓展了云南山水画创作的途径,同时也揭开了刘汝璋山水画的一个迷局:亦即可行、可游、可居者少,可望者多。古人云:“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现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有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本意。”(郭熙,《山水训》)而刘汝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知道由其他时空而来的语言体系,是解决不了云南山水画创作的问题的。所以,他是一个山水画创作的边屯者,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忠于作为客体的山水,找到符合云南山水画创作的语言体系,就是他精研山水画创作数十年的意义所在。
生有涯而知无涯,刘汝璋作为一个艺术的边屯者,在自己的精神的栖息地中耕耘收获,想必就是幸福了吧。在这里,诚挚地祝展览举办成功!
2017年9月6日星期三于司家营龙头街
刘汝璋艺术简历
刘汝璋,1943年生于丽江市永胜县城,曾供职于县文化馆。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入选文化部、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首届中国画展、第八届全国美展、跨世纪暨建国50周年全国山水画展、“中亨杯”全国书画大展等,香港回归全国书画大展获佳作奖。多次入选全国群星奖并获优秀奖。曾有多件作品参加对外展出。
退休后,先后受聘在云南艺术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任教。云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2008年中共丽江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授予宣传文化突出贡献奖。2016年获丽江市首届“蓝月亮”杯文化艺术综合奖特别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