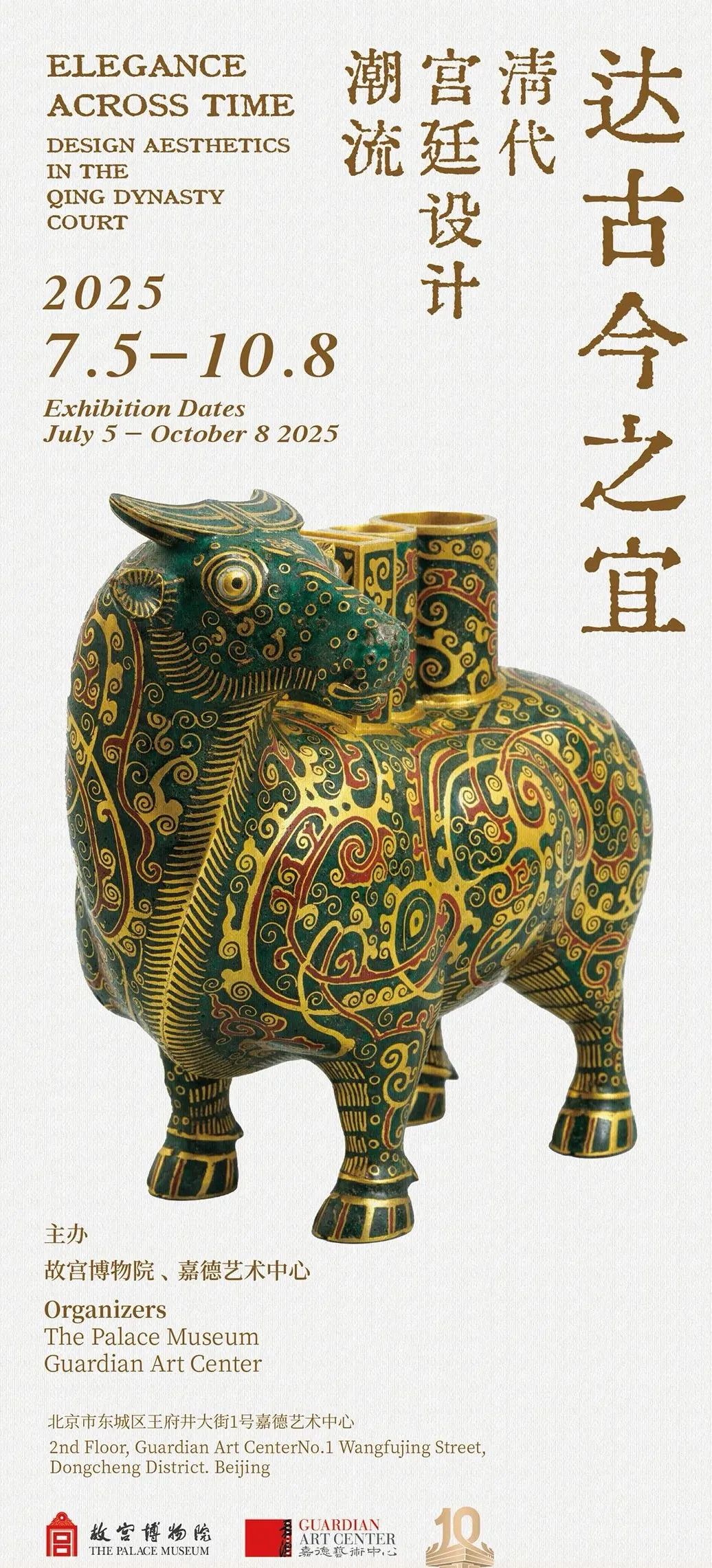我的眼睛落在张瑜娟的画上时,一时不能移开,这是什么东东?为什么这样画?画的是什么?
这不是山水画,也不能叫做人物画,但画面上的确有人物,而且是极具张力的人物,他们或躺或坐,或者背对着我们兀自向天而歌,他们没有与现实中的我直接交流,却带着我的情绪上下翻腾,左右挪动,似乎在打通彼此能够交融的通道,只有戏剧才能给人这样的感受。
对了,戏剧!这是我所熟悉的,她们不需要大的舞台,就表现出极其宽泛的时空容纳性,没有边界,却能够毫无障碍地从一个空间跨越到另一个空间。中国戏剧,几人没看过?无论京剧、秦腔、昆曲还是越剧、黄梅、各地梆子,谁的心灵没有被紧锣密鼓的敲打或激越高亢的唱腔震撼过?那抬脚踢腿、水袖挥舞,不用解释,就能看出是出门进门或者翻身上马,不用字幕,也能读懂角色的苦闷、忧愁、喜悦、期盼,更不要说那饱含激情的唱段,简练优美的词语,时而是穿越千年的豪迈,时而是拨动神经的颤栗,中国戏剧,是如此的丰富出彩,又如此的富有表达力与感染力,或者说:如此具有艺术的魅力!
当然,张瑜娟画的不是戏剧人物,更不是戏剧场景,否则也没有什么疑问可说。无论什么艺术形式都是用来揭露人类的真实存在也是反映艺术家的真实想法的,我面对着张瑜娟的画面,一时有些紧张。这些我不太熟悉的图式,正攫夺着我,我想要挣脱她,更想要了解她、探索她。
面前是这样一幅作品,图面上有许多的人物,更有远远近近、大小不同或清晰、或虚无的空间,人物没有精美的外形,没有细致的装扮,甚至于没有清晰的轮廓,更不要说被修饰了。但他们却真实地存在着,不仅仅是存在,你仔细看,有的像是进入深度睡眠,正在虚幻中庄子梦蝶;有的却在做着明显的肢体语言,仿佛想干些什么;有的虽然背身而立,但昂扬的头颅,直立的长辫,如被长鞭猛抽,带着强烈的肌肉痉挛的动感,或者是刚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呐喊,你能感觉到他们引发的气流,当这气流从你身边经过时,你不由得心里一缩,浑身一紧,自己愤怒时、悲伤时的各种经历,即刻重现。
张瑜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她又是为什么要如此地激愤?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否定自己的作品更悲惨的了。年少而酷爱绘画的张瑜娟确定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我要画画,考上美院!她做到了,那一年,西安美术学院国画山水专业只招收十来名学生,她就是其中之一。从中学就天天站在大街上画速写的功力,四年学院严格有效的专业教学,她成为一名传统的山水画家应该说是顺势而为的必然。
但她没有按照别人以为的那样走下去。有一天,推翻了自己的画风,从具象到抽象,从山水到人物,似乎是承接使命一般地选择了改变。
为什么?
她轻轻一笑:思考。似乎没有痛苦。但她说,思考的过程就是痛苦的。
我与张瑜娟深谈过两次,这两次我们多次谈到自己看过的书,人生最得意的莫过于有人懂你,哪怕只是在一个点上的会心一笑。从宇宙起源、平行空间到目前很火的智能机器,再回到百谈不厌的文化艺术、绘画小说,尼采、黑格尔、博尔赫斯、卡夫卡等人总能唤起我们的热情。
对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张瑜娟的绘画与博尔赫斯的小说!模糊真实的时间,虚构空间的界线,又像卡夫卡一样,语言有很大的跳跃性与象征意义,人物似乎是充满张力的,又似乎是无力的。
但张瑜娟的作品又明显地是自己的,如果让我粗浅地形容她的作品,我更愿意用“冥想”这个词,或者说蒙太奇。
我站在张瑜娟的画作前,画面上的空间不是机械的排列,那种连绵的通透的不用切换却能流畅地进入的自如,满足了我对平行空间的想像,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地置换现世的你与另一个空间的你,一定有许多的人愿意去试试。在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探索中,应该有一条秘密通道存在着吧?
张瑜娟也是一位诗人,一位作家,我读过她的文字不多,但对她的敏锐与细腻印象深刻。她的文字像一把细小而犀利的手术刀,不见血流,已然拨动神经。
这样的张瑜娟,这样的作品,是姹紫嫣红的春天中很特别的一朵鲜花。如同艺闻空间,不豪华,不张扬,却总能把与众不同又耐人寻味的作品奉献出来一样。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张瑜娟,了解她的作品,就象熟悉艺闻空间不断推出来美化我们生活的作品一样。生活这么多样,又这么美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读你百遍也不厌。
杨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