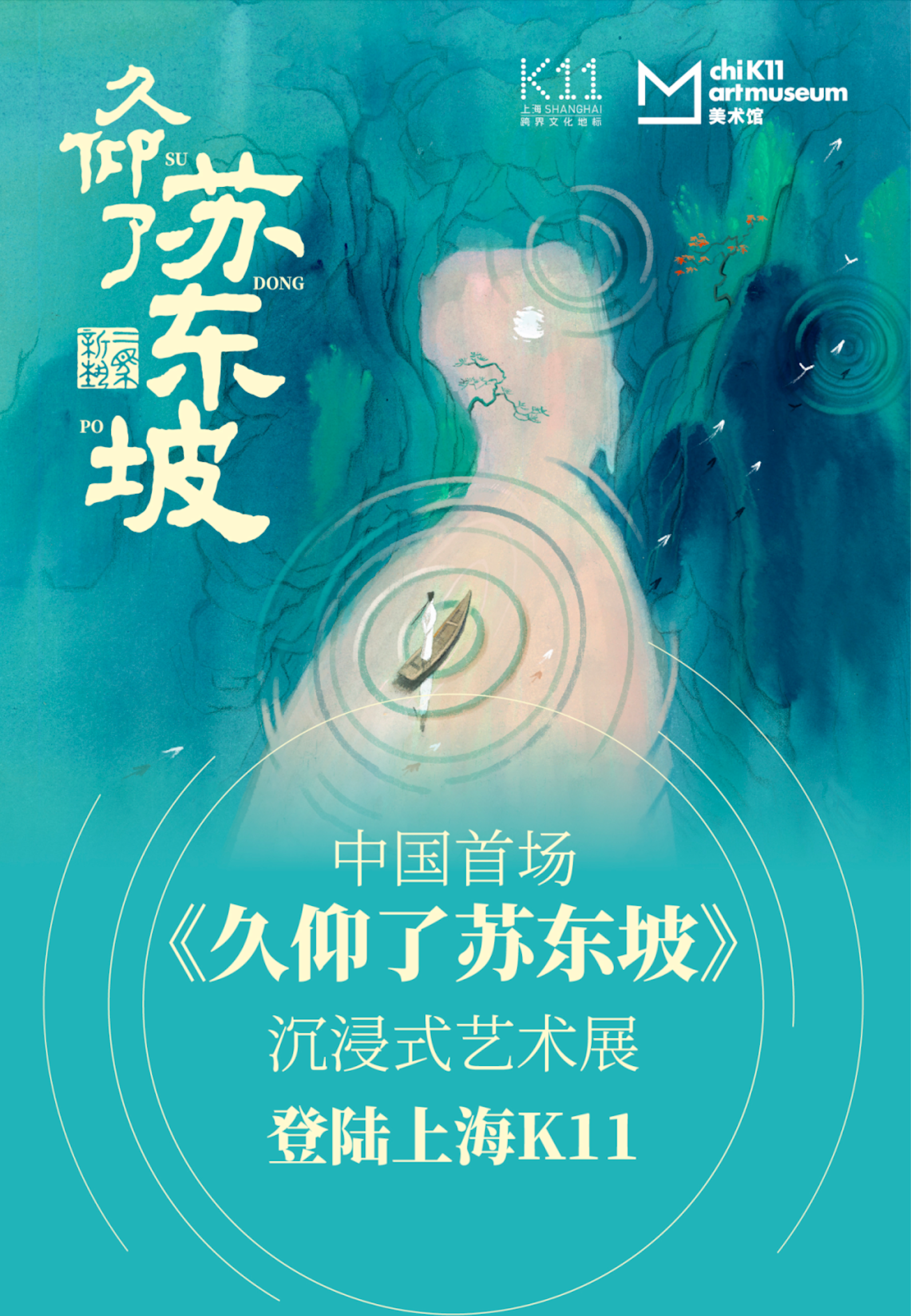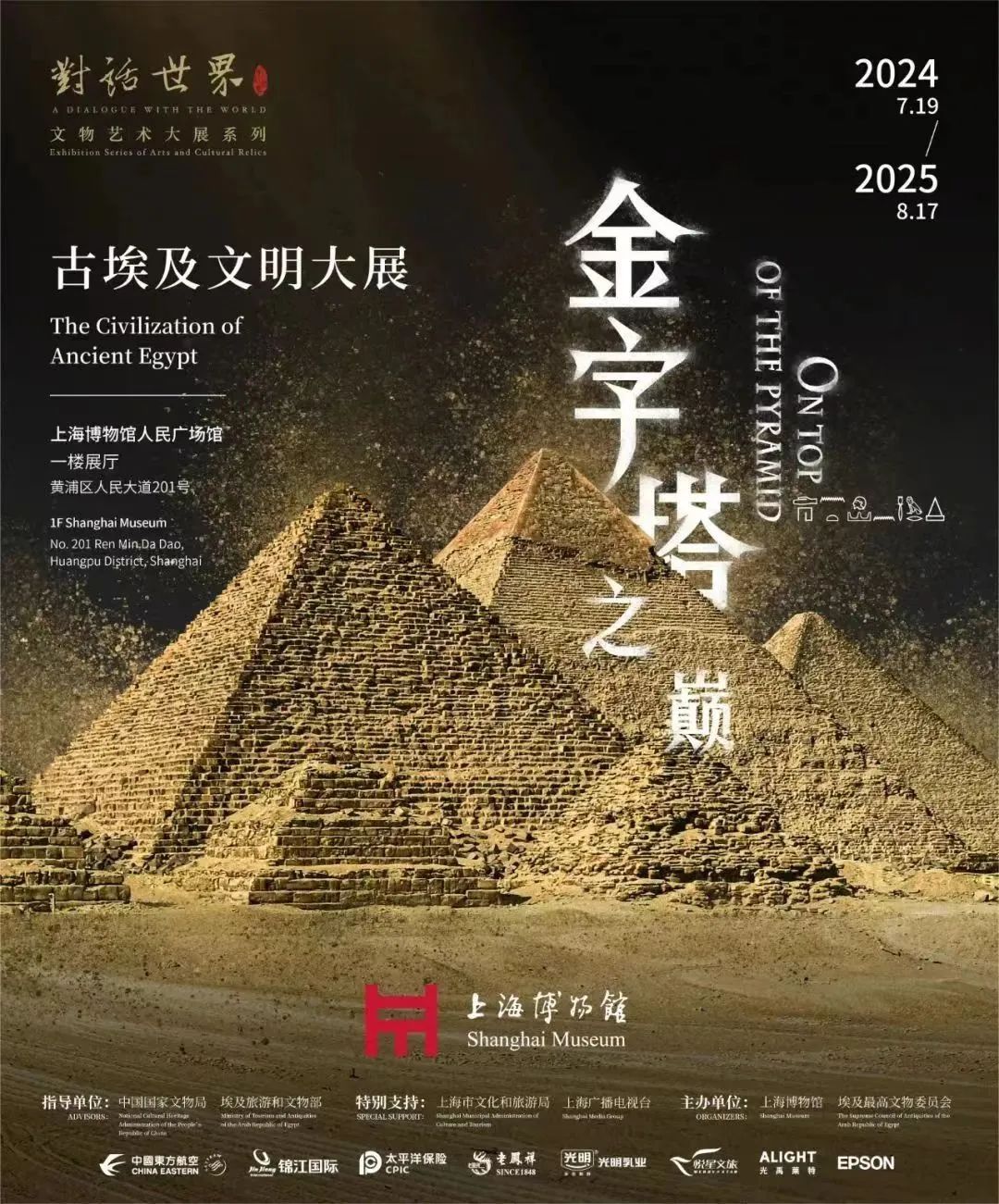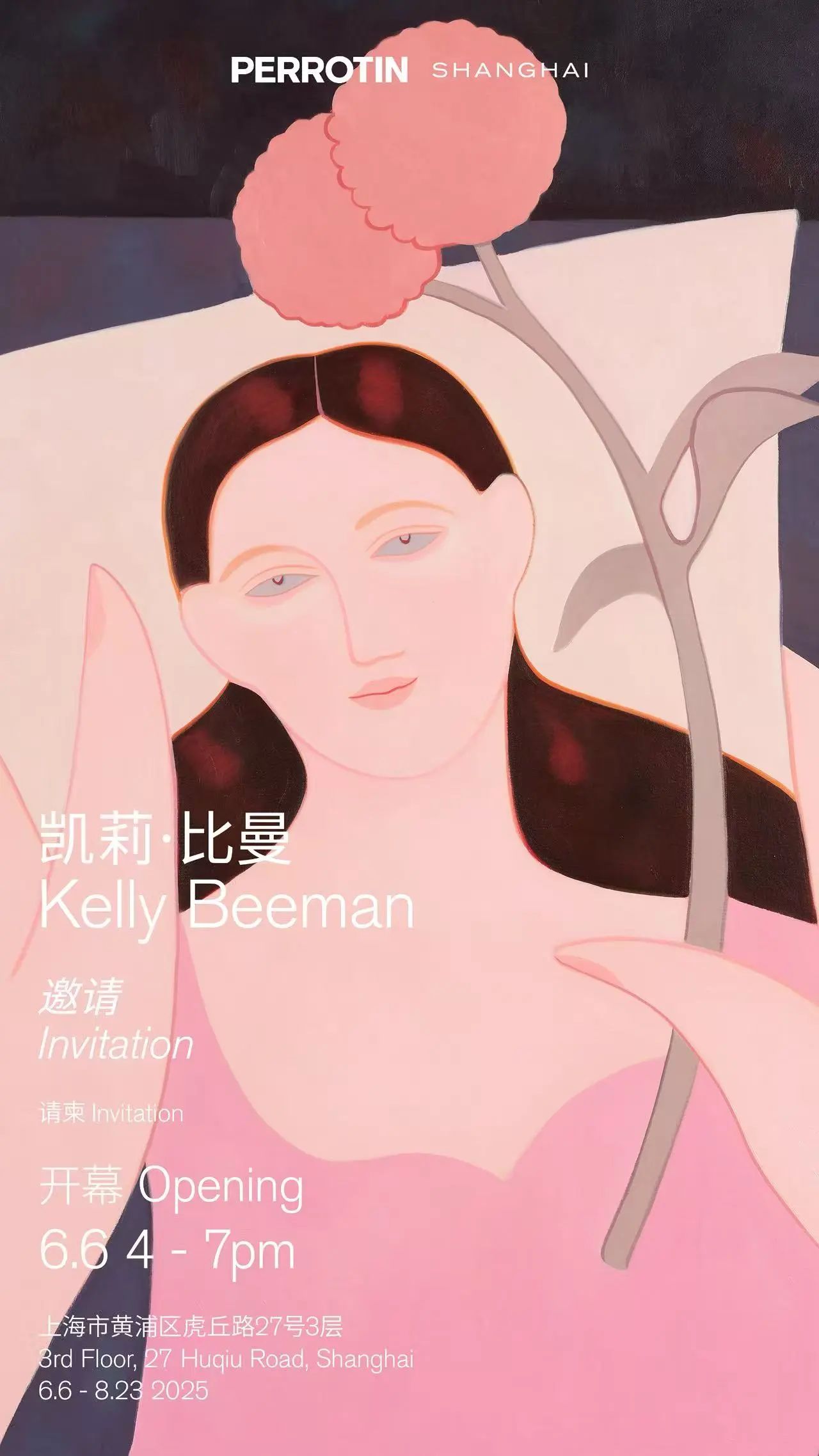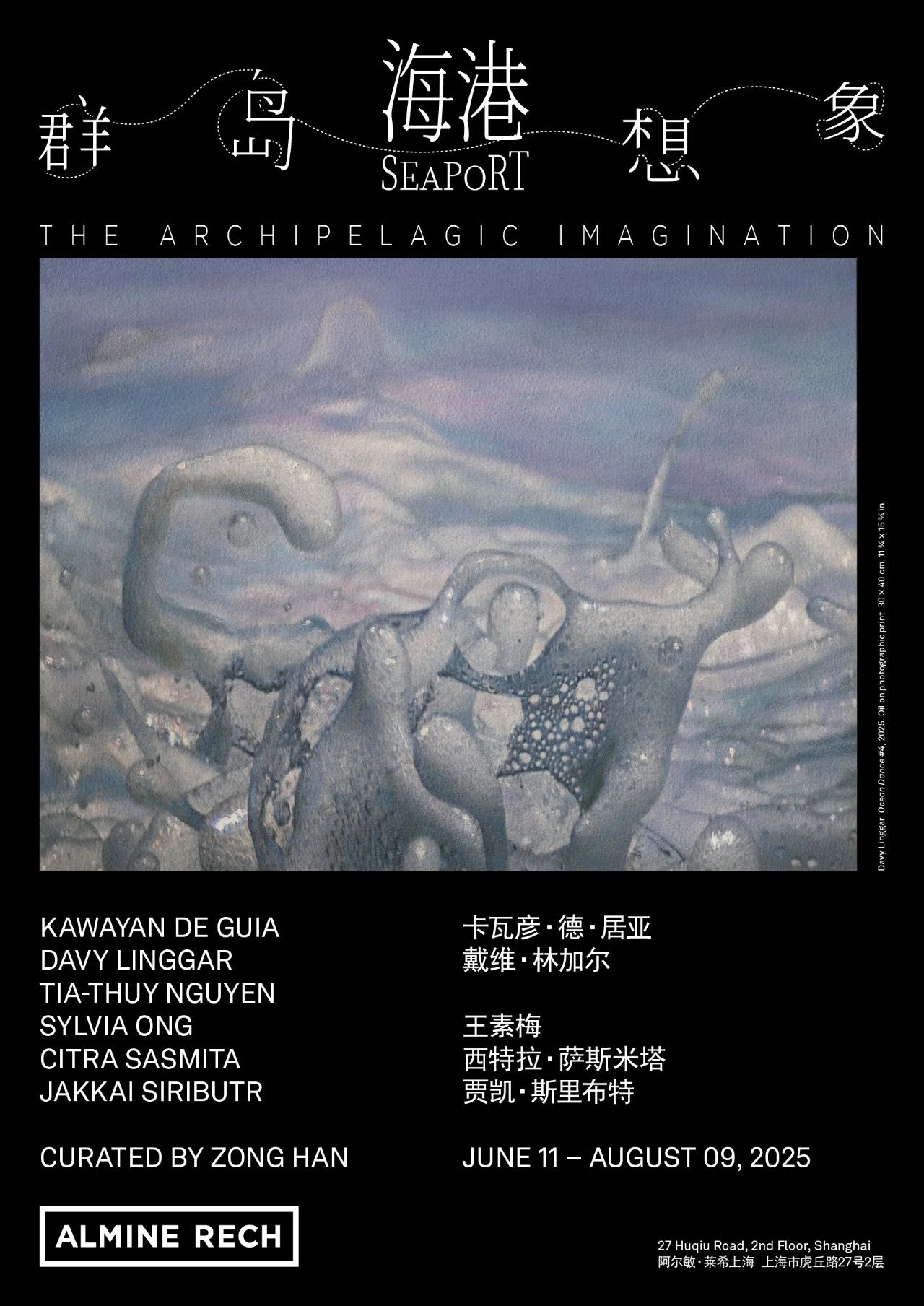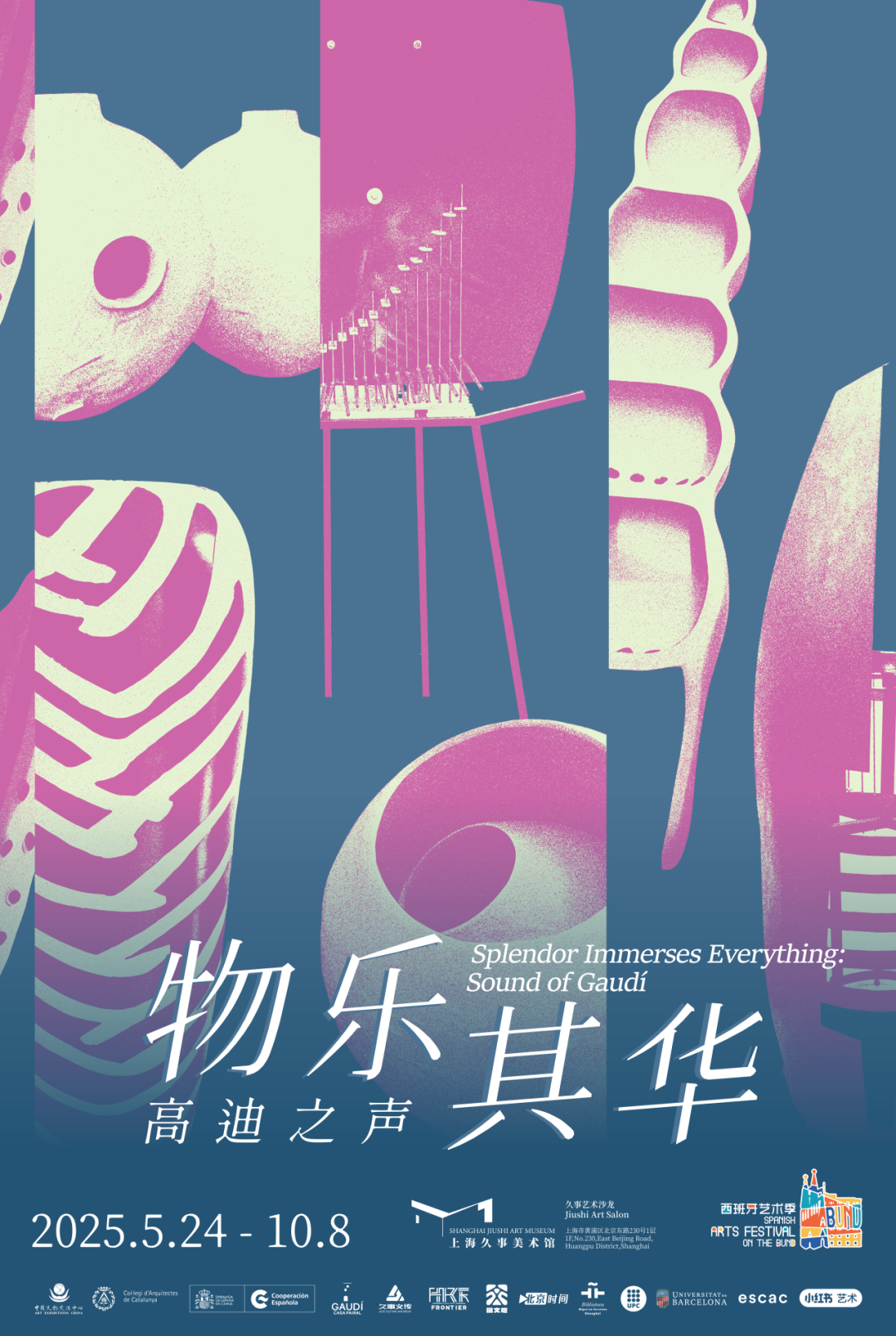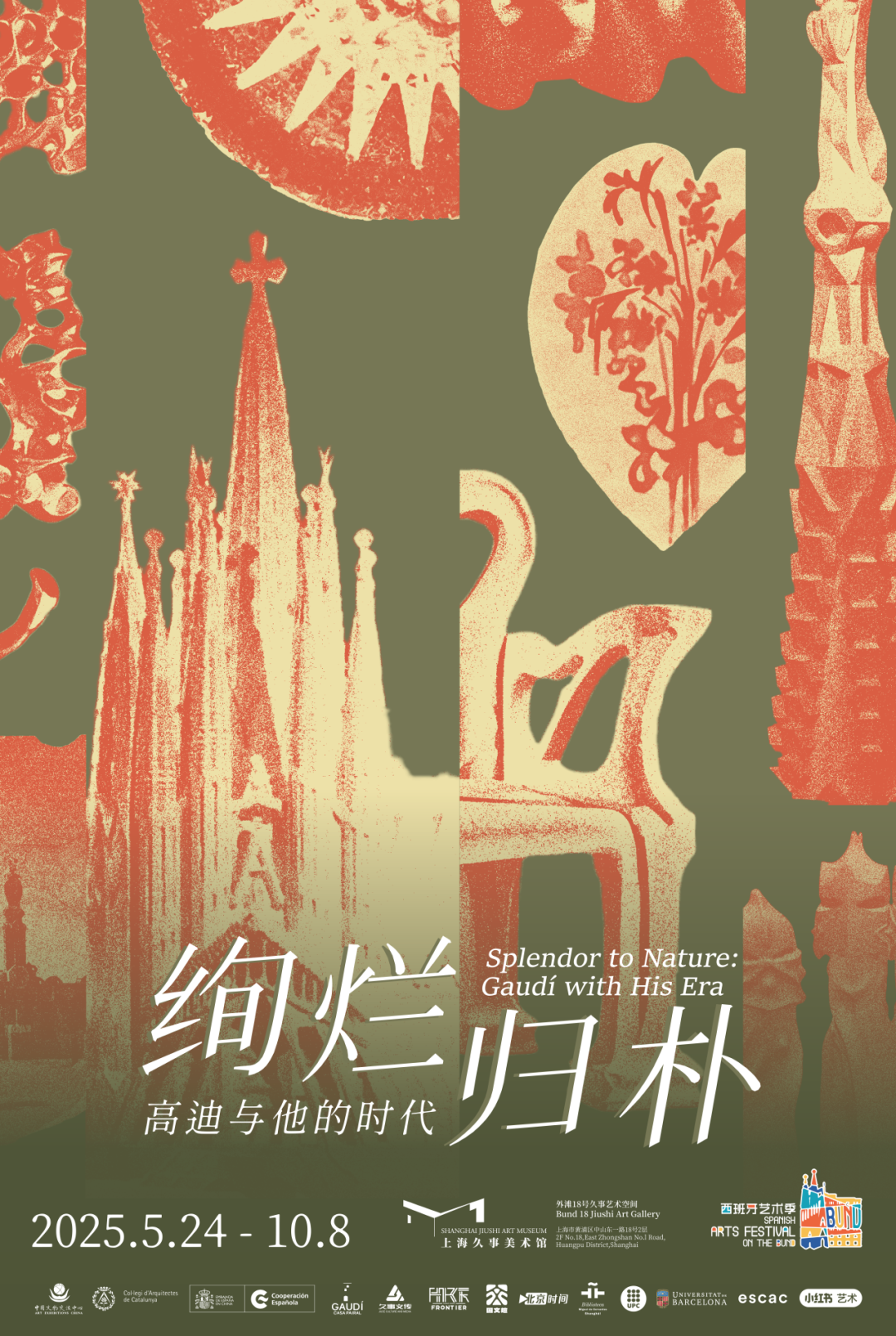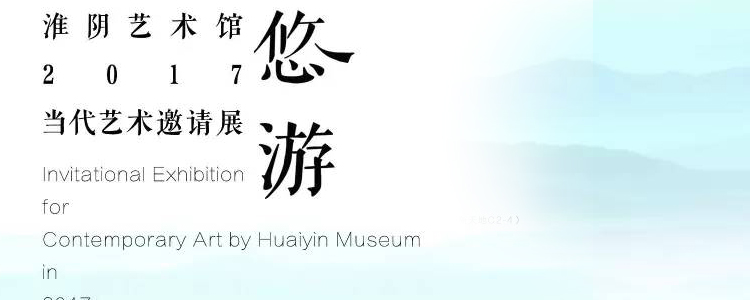
悠游的理想
写在“2017淮阴艺术馆当代艺术邀请展”开幕之际
文/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陈晶
“2017淮阴艺术馆当代艺术邀请展”将展览定名为“悠游”,出其不意,也合情合理。在上满了发条的都市机器运行中,“悠游”实在是一件奢侈得令人不由神往的事情。关于“悠游”的遐思,只适合安静的心境。入夜,打开电脑,15位画家风格各异的画面不断撞入眼帘,窗外月色如水,心也悠游开去。
游,是中国文人画的美学追求,“可游、可居”,宗炳“卧游”,寄情山水、物我合一,借画抒情;游,更是中国文人的理想生活境界。庄子之谓“逍遥游”、郭熙之谓“林泉之志”,孔子也向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本质有别,但在追求不为物所滞,自在自得的生活旨趣上是一致的。这种审美化的诗意生活的情结,在中国文人的文化基因中代代传承,已成为一种最高理想的人生境界。
悠游,比之逍遥游少一分浪漫不羁,多一分内心的笃定,更偏向于儒家的色彩。此次展览所汇聚的画家,即非隐士,也非泥古不化,他们的生活状态实际上积极入世,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使命感,一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但同时骨子里相当清高地经营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着一份中国传统文人对人生的诗性领悟。正如学术总监沈伟秉持的艺术批评原则“知人论世”,此番“悠游”展油画、水墨兼顾,具象、抽象均沾,表面看仿佛拉拉杂杂,但暗含的线索其实是人,他们的艺术互有关联又自成风格,像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像素点,在策展人的选择下,汇聚成一群志向相投之画家在当下共有的精神图像。
总之,这是一个有趣的展览,从策展人到参展画家,每一个人都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谜面,谜底则在时代与个体、作者与观者的叠加中隐隐若现。
一、文化冲撞和现实的隐喻
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展,艺术语言的探索性和当代文化的反思性是展览叙事的重要特质。在这次展览中,“悠游”的古典语汇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必然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文化冲撞,也必然回望来时路,探寻根源。因此,展览中不论是油画、水墨,甚至是综合材料,作者文化根性的共鸣,使展览呈现出气质上的一致。
曹跃的画面的锈蚀沧桑,像是历经久远的沉船上沉寂的物件;陈向兵笔下野草疯长、光斑闪动,犹如疾驰而过的窗外掠影;文祯非将日常所见的符号堆叠在画面上,创造着熟悉事物的特殊视觉感受;王东春在偶发即兴的笔触中逐渐显影,试图在凌乱中建立秩序……他们随机运用分属于不同时空的典型物品,进行信息编码,闪动、不稳定、不确定和疏离感是几位画家的共同特点,画面如同旧胶片上跃动光斑的晃动影像,在历史与现实的冲撞中,令人觉出世事变迁、繁华浮世的隐喻。
王长明将文人赏石、八大的水鸟与各种现代图像进行并置;魏志成同样运用挪用,超出逻辑地并置不同的生活情境,他使用数码的方式来设计草图,然后再进行绘画表现,这本身就具有了当代思维的特征,打乱逻辑、荒诞叙事,营造出一个我们似曾相识,却又无比陌生的碎片化世界。不同的是王长明借用了波普的方式,而魏志成更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气氛。戴少龙喜欢画北方憨厚的少妇和羊,大红大绿的对比配色和粗犷的人物形象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寻根的气息,但从接近毕加索画法的线条穿插的羊的形象,我们仍可以看出画者将中国的民间审美与西方现代艺术打通融合的努力。
事实上,展览中相当一部分画家的作品都流露着西方绘画的解构思想与中国绘画的意象交融,他们试图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进行现代语境下的叙事重建,或者从图像上,或者从媒介上,努力进行着相互碰撞、包容的中西古今的对话。
二、形而上的乡愁
“然而我们是谁? 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是一次偶然地跌入世界?”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发问,为什么人们会对这样形而上的哲思义无反顾地探究?海德格尔用诺瓦利斯(Novalis,1772年——1801年)的诗回答道:“哲学就是怀着乡愁冲动的人四处寻找家园。”人们居于大地,我们整体的生存受到乡愁驱动,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因为我们不得不寻找家园,安放四处游荡的心灵。
不知为何,展览中许多作品都令我想起海德格尔笔下的乡愁,他们用不同的诗意的绘画语言,追索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薛扬与谢海都在解构传统的笔墨语言,用不同的方式构建诗意的画面中的哲思。薛扬较为具象,符号化的表现湖山、园林、赏石等这些江南文人的寄情之所,有着魏晋山水画的单纯古拙,静美而寂寥,但画中常突兀地伸出一树横亘其间,或是隐喻对家园可望却不可及的惆怅。谢海的抽象水墨,则是静水深流,单纯的形式中涌动着丰富和激烈的变化,大体量的墨色并不死寂,浓淡和笔法的变化令墨色时而通透,时而浓重,仿佛有灵光挤开层层叠叠的深邃的浓云,从裂隙中迸发出来。谢海的画题是读画的重要契机,画题出其不意,又引导你走向某种意象和顿悟,严格来说,这不是纯粹的抽象艺术,倒是更具有东方禅画修心观境的意味。
比较下,朱志刚、张展、李鹏的画在抽象的路上走得更远,摒弃表象的浮光,追问更加本体性的问题。尤其是李鹏的抽象,干净、通透,混合着冷静的理性和优雅的抒情,正如李建春评论他的画,简单得如同一个优美的休止。是的,在喋喋不休的世事中,返还内心的超然、自在,也许只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休止。
“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19世纪早期,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这段演讲词,似乎仍可作为现代人追寻乡愁、反观内心的现实处境之写照。这也呼应了策展的主旨:只有从功利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轻功利而游于艺,才能寻得乡愁,悠游于诗意的生活。
三、心灵的私语与精神图景
中国传统文人美学观念强调创作主体主观情感的抒发,而这种抒发恰恰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经历与感悟之中,再通过作品表达传递出来,实现自己心中所追求的自由。身处现代,并不见得会刻意追慕古人,事实上谁都无法、也没必要回到过去的语境,但是对心灵自由的企望,对高度审美化的人生的追求,仍然是一脉传承。本来艺术就不仅仅是人的情感表达或精神需求的满足,更重要地在于,它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诗意生存的方式。
封加樑、王清丽、谢中霞都擅长表现私人化的情感与欲望,但各说各话。如果说封加樑的绘画中笼罩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1939年)式的压抑,我们或许更容易理解画家笔下的欲望与深坠其中的失落。王清丽的色彩感觉极好,无论是浓烈饱满还是朦胧柔和的色彩调性都游刃有余,明丽的色彩、干脆豪放的笔触一如其爽朗的性格;谢中霞的画面与之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飘忽迷离,如梦似幻,色调优雅迷人,亦如其含蓄内敛的性情。马与人的图像在两位女画家的笔下反复出现,王清丽画木马,在既定轨道上飞速旋转,追逐、逃离的游戏不断上演,周而复始,永不可及,恰似我们所陷入的世界。谢中霞画林中之马,如同朦胧诗一般带着些许伤感幽怨,离愁别绪,这是她的敏感的情感世界,如同与这个最好的时代的一场爱恋,有爱、有怨、有幻想,正如谢中霞说:“不管生活怎样,我们还是会向往!”两位女画家从女性丰富细腻的感知出发,表达极为个体化的生存经验,在心灵的私语中描绘着情感的图像,宣泄画家的强烈情感与真实体验,那是心灵深处的“我”与现实的“我”恳切而无声地心神交会。
想起宗白华先生曾写下一首《生命之窗的内外》:
生活的节奏,机器的节奏,
推动着社会的车轮,宇宙的旋律。
白云在高空飘荡,
人群在都会匆忙!
……
是诗意、是梦境、是凄凉、是回想?
缕缕的情丝,织就生命的憧憬。
大地在窗外睡眠!
窗内的人心,
遥领着世界深秘的回音。”
1980年,李泽厚在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所作的序言中,曾经引用这诗中的句子发出感慨:在“机器的节奏”愈来愈快速,“生活的节奏”愈来愈紧张的异化世界里,如何保持住人间的诗意、生命、憧憬和情丝,不正是今日现代社会中值得注意的世界性问题么?不正是今天美的哲学所应研究的问题么?
今日,物质丰裕时代的焦虑恐怕更甚于李泽厚笔下的当年,而唯有美与艺术不可辜负。暂时远离车马喧嚣和繁杂俗物,在美学的馨香中散步,在艺术的幻境中悠游,至少在这个时空,不受物欲之制,心灵畅达,悠游自得,这是策展人的理想,也是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奢侈的馈赠。
2017年7月2日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