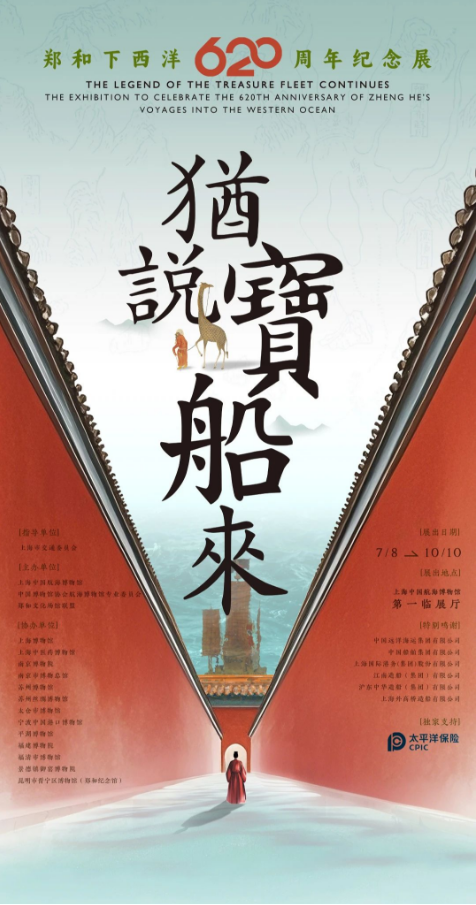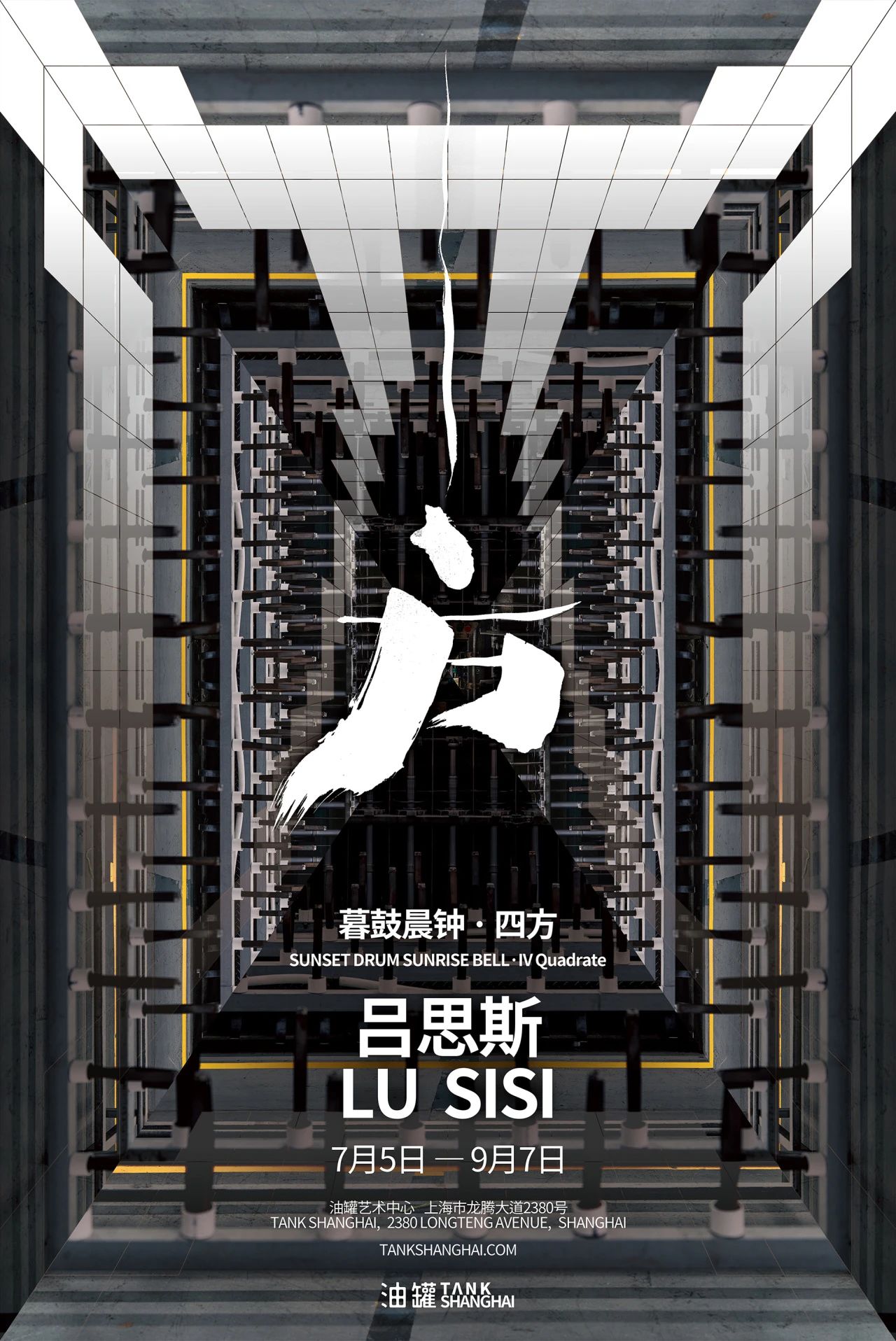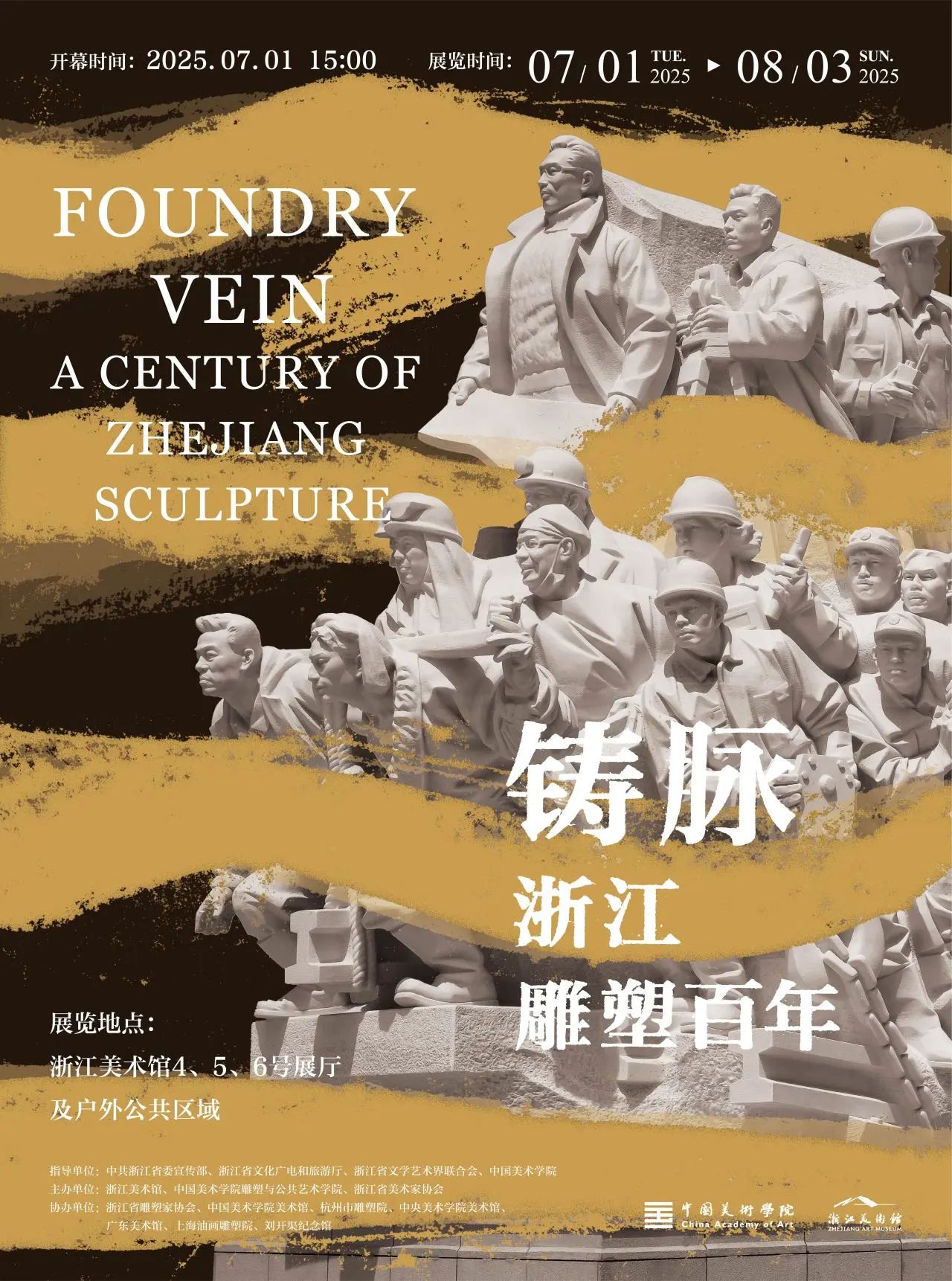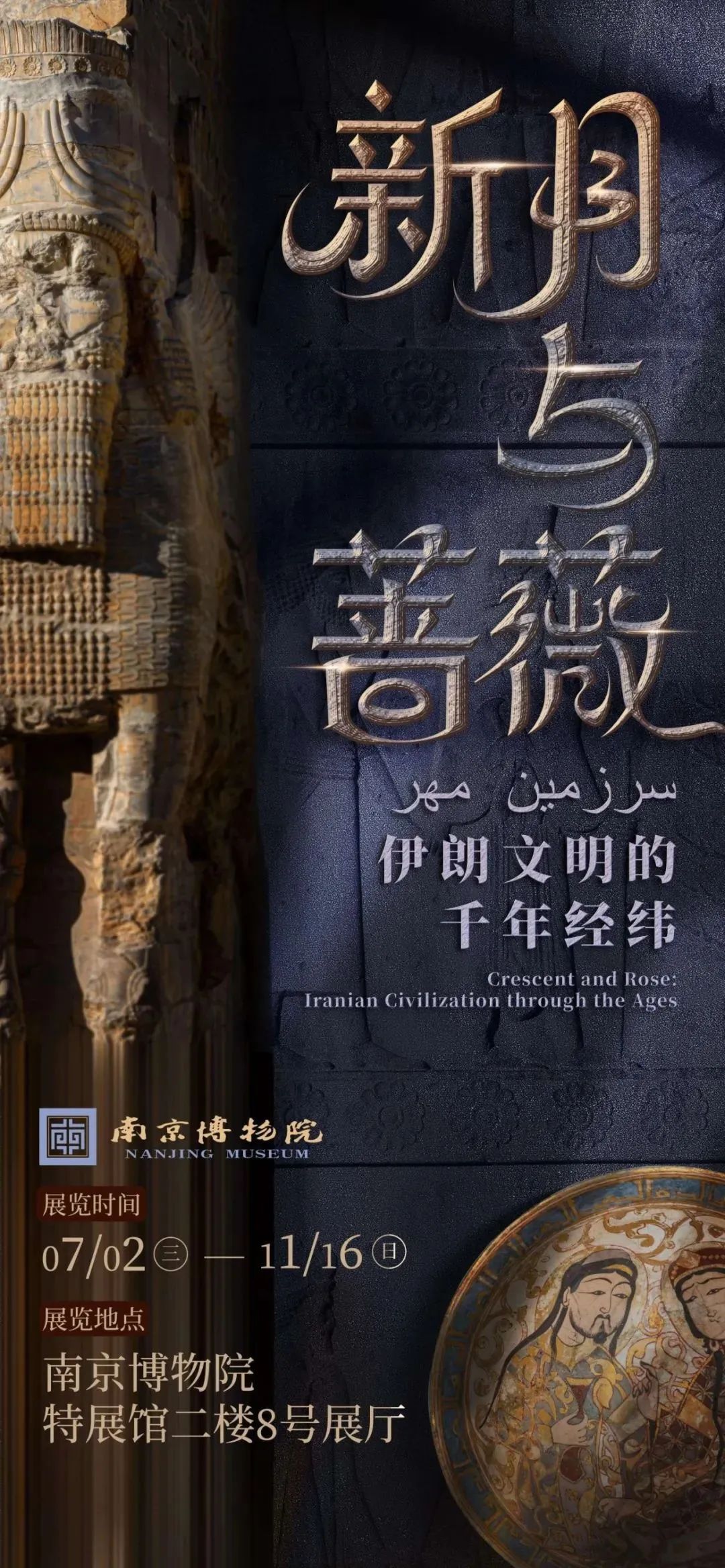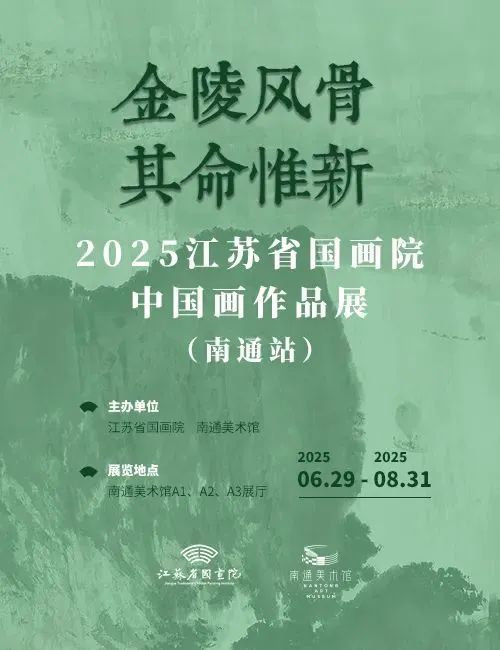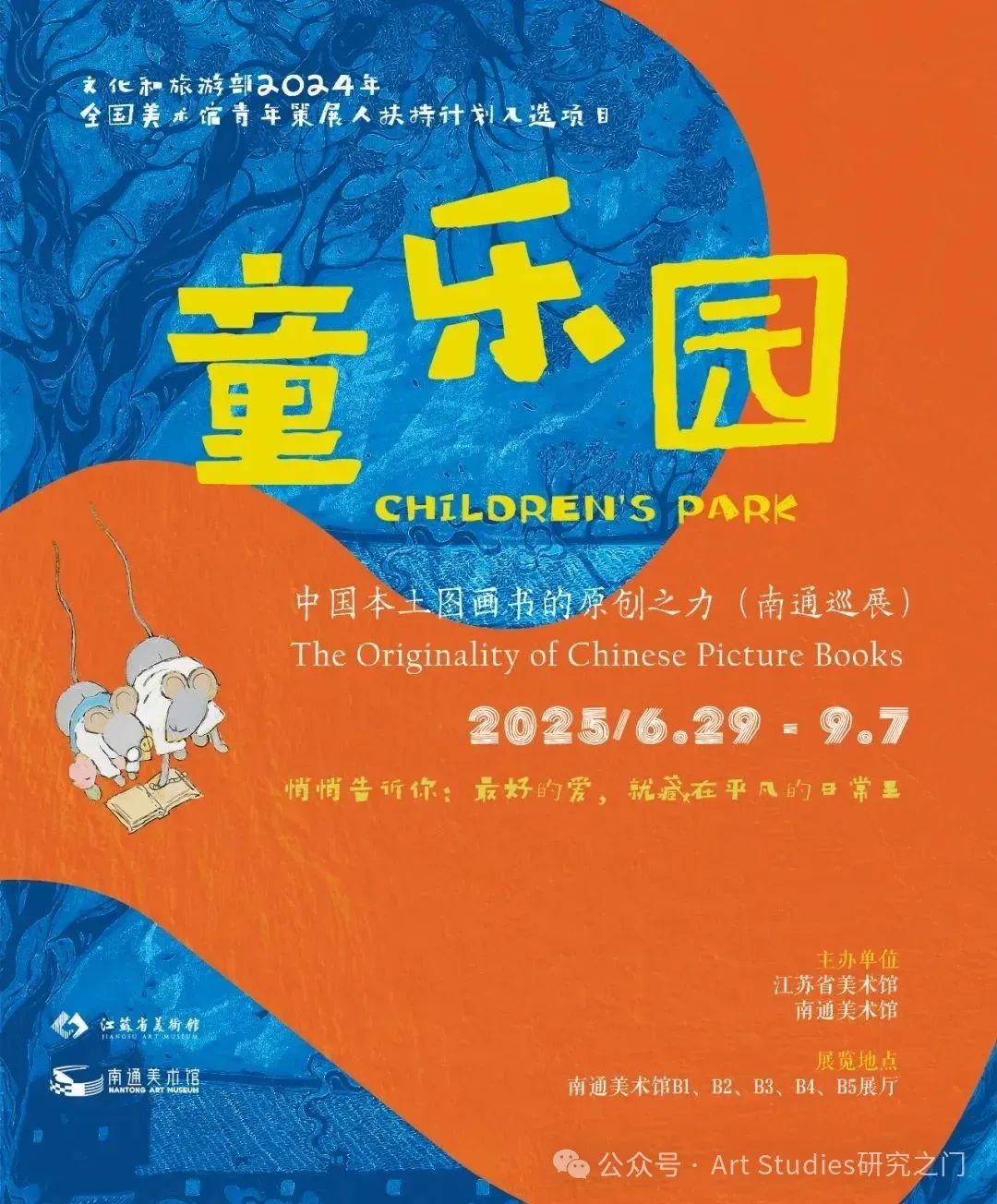行万里路,画千张画,写百家人。对一名画者来说,58岁是走遍千山万水的最好年龄。李之河是勤奋的,人物写生是其创作的根。隔三差五,闲不住的他总要来到海边,到黄土塬上,到云南,婺源,山东,新疆,到塞北杀虎口……到某个谁也想不到的陌生所在,静静住上一段,然后满载而归,每次不亦乐乎。
李之河的水墨写生人物其实“出身江湖”,并非严格意义的学院派,然比之并不逊色。他的一部分创作还试图表现出时代性和使命感, 颇有特色。他的人物形象里有猴气,又不乏静气,合规矩,又不缺野趣,一反平俗,带有湖州人独有的灵气。重画面感,直击眼球,颇合其爽朗个性,路属阳刚,与其版画异曲同工。
与“搜尽千峰打草稿”不同,李之河的水墨人物则是“凡写一人即成品”,很有在写生中直接现场创作的特点。尽管他的画法兼有中西结合形式,语言线条常呈复数特点和复线特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画线条,但这种画法的别样传神,既无碍于其作品的灵性,更无损于他作为湖州第一位加入中国美协会员的名实。
工作室是李之河对他的写生作品再完善的地方。
走进李之河的工作室,你会发现各种石头。李之河自号“河石”,酷爱石头,工作室收集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件物什都连着他一个个写生故事和当地传说。古拙的六安绣品,各地的古旧玩意,都带着淳朴的气息,在你身前身后探头探脑。阳光大方地洒在落地窗玻璃上。阳台上不同的花草和来自大山的紫藤在微风中摇曳。青卞山就在隔窗不远的地方,西苕溪在脚下缓缓淌过。
可水阁,这是一位见过所有沧桑却未必承受过所有沧桑的时代艺术幸运儿的工作所在。太阳是如此温暖。一个最好的时代,容忍了一位有天赋的青年在艺术之河里终生尽情遨游。李之河是幸运的,更是刻苦的。画桌与毛毡足够长,以便容下六尺写生大画。一根根人物线条随着古典音乐弥漫开来,在宣纸上缓缓舒展,继而生动起来。其实这种环境下的工作已经经历了之前写生的思考与痛楚,不再是简单的描摹,而剩下更多的自洽和愉悦。只要不是外出写生或者参加必须的艺术活动,李之河每天大多数时间要沉浸在工作室里,忘我自乐。
在大量写生创作之余,李之河从未忘记传统艺术事业的承继以及自己作为文化馆研究馆员(正高)的本职。版画创作工艺的复杂性使之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代青年中普及率并不高,作为鲁迅版画奖获得者的他常对此忧心忡忡,而湖州国画家长期由于本土优越感滋生的闭塞性和书斋气,又催生出他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坚决一改故旧习气,走出象牙之塔,投向现实百态,通过写生试图呈现出焕发着时代生机活力的新作品。他之前成立的公益性“晟社版画高研班”和“兴吴社群众艺术团队”为他工作室的普及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后续深入的探索使他的团队成员在传统版画创新和国画写生创作方面已呈佳绩,屡屡在全国和省市大赛中获奖,渐成浙北群众艺术普及工作的小荷一角。
读着李之河的一幅幅水墨写生人物,看着他工作室内的每一件古旧玩意,你仿佛感到此刻正穿过雅品的骨头,抚摸自己的慢生活。
李之河的书房兼储藏室呈橱柜式,除了大量美术书籍,分类存放着近四十年来的各种写生作品,草稿,想法,以及创意构图。最近,李之河越画越感到自己时间不够,我是深知的。在他这样的年龄,对于能够腾出大把的时间更纯粹地去做自己喜欢和想做的事,总有一种莫名强烈的饥渴。这种焦虑在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曾经的时代耗去了我们太多的青春,以致在一个不再年轻的年龄,还存着一颗年轻的心。他们曾经不为自己活,所以有太多的事要做、想做、没做。
这种状态就叫作执着,沉醉。如一个纯净如水的实在念想,在某日清晨,突然醒来。
2016年12月9日 费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