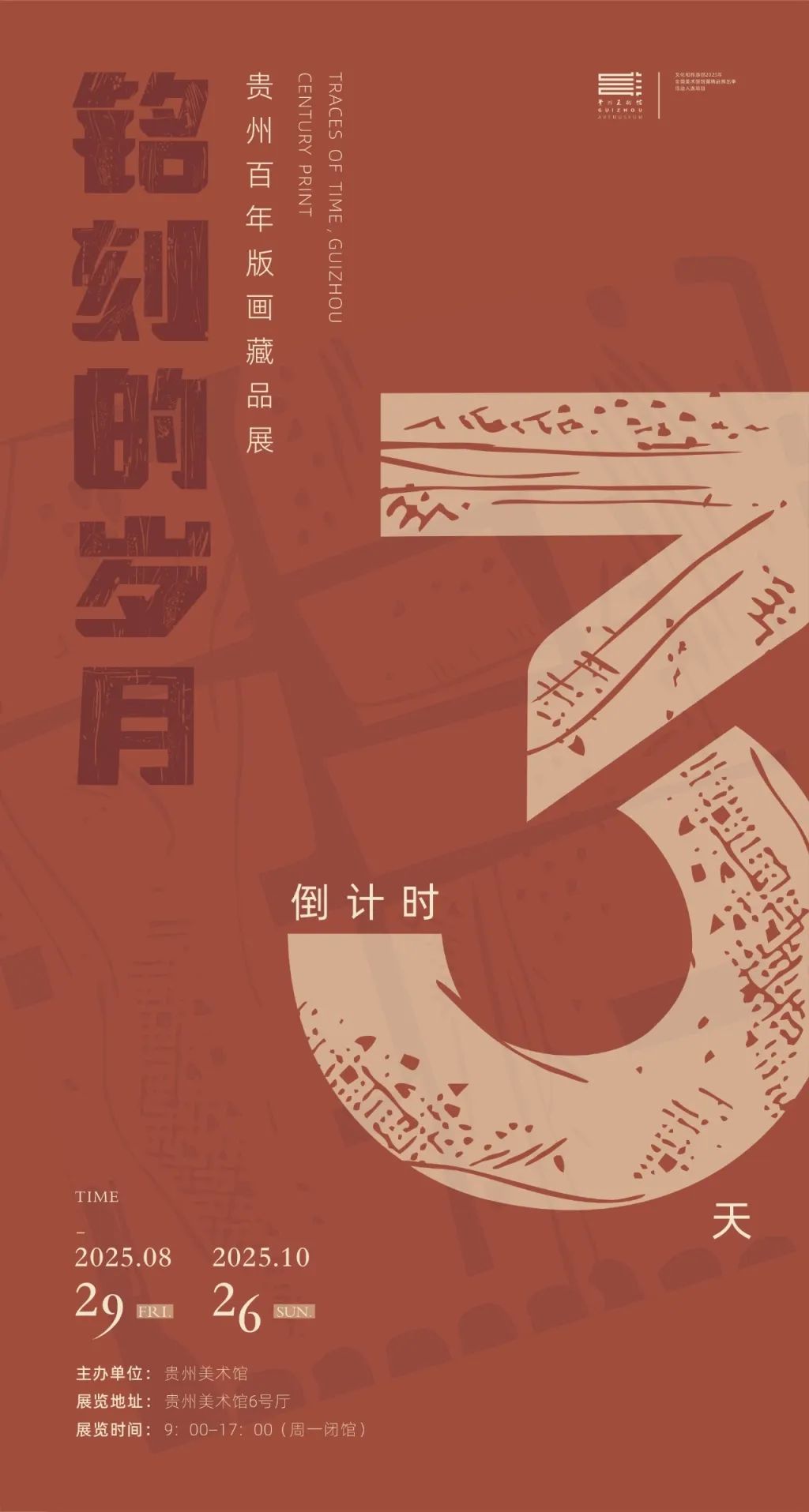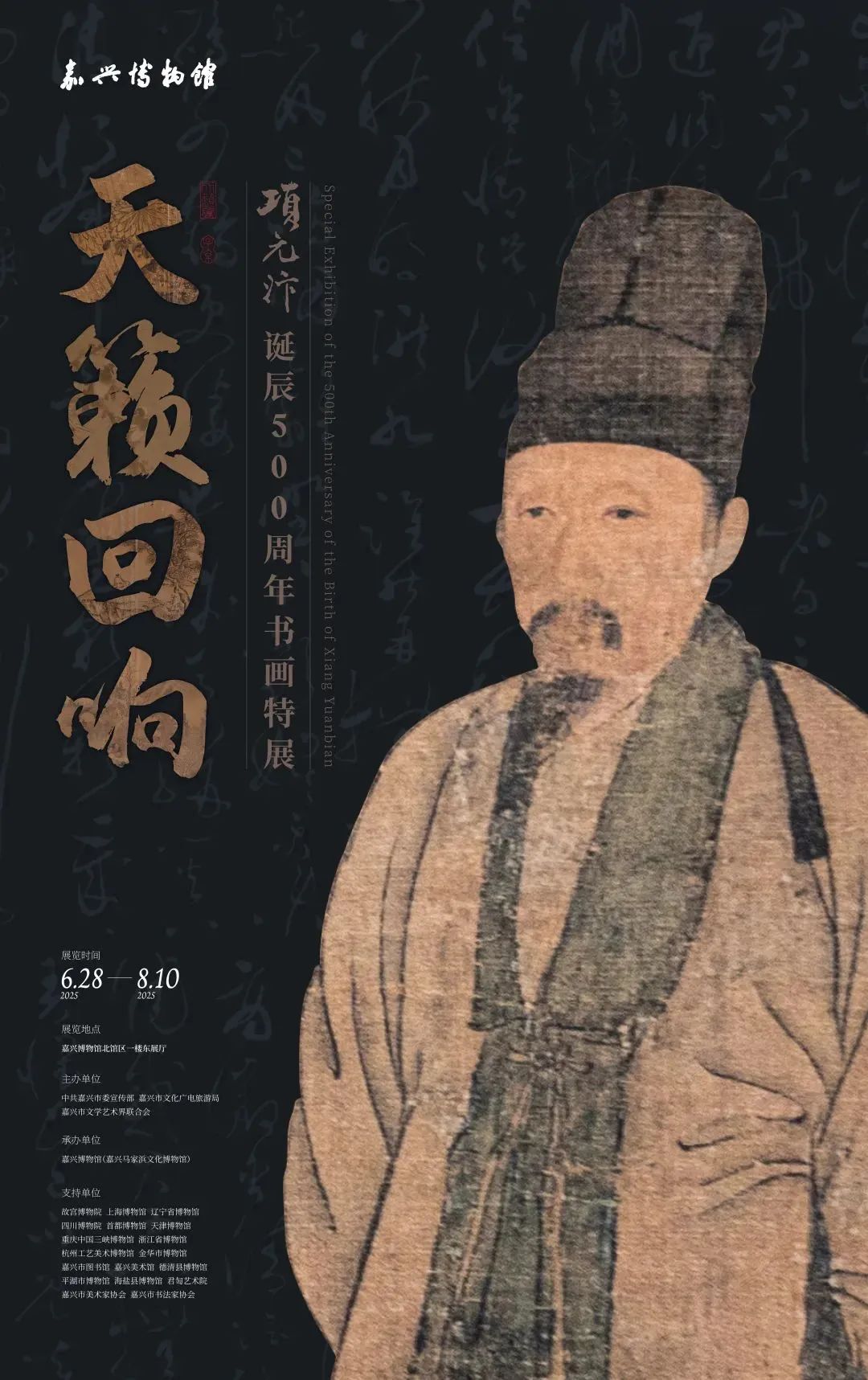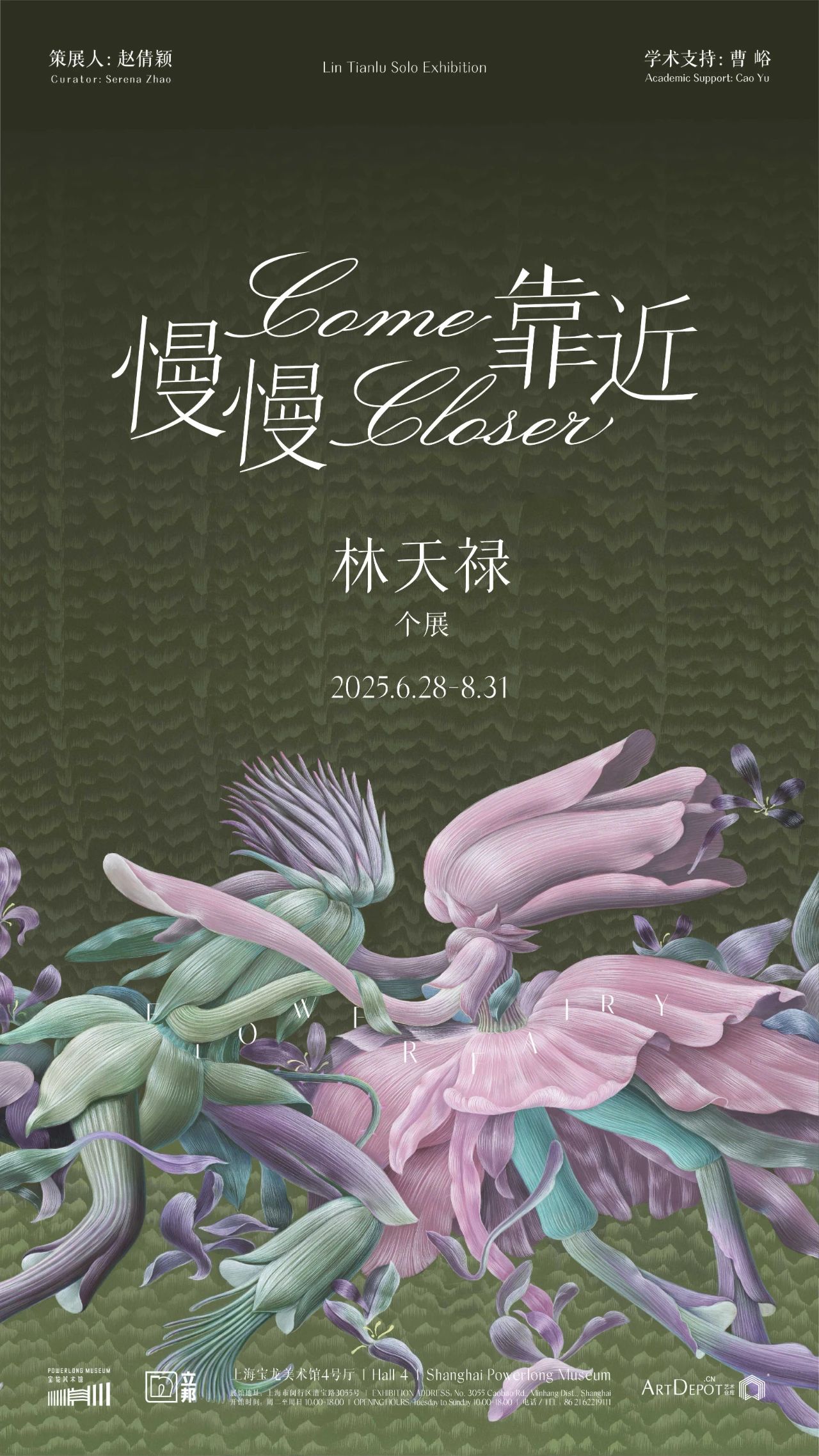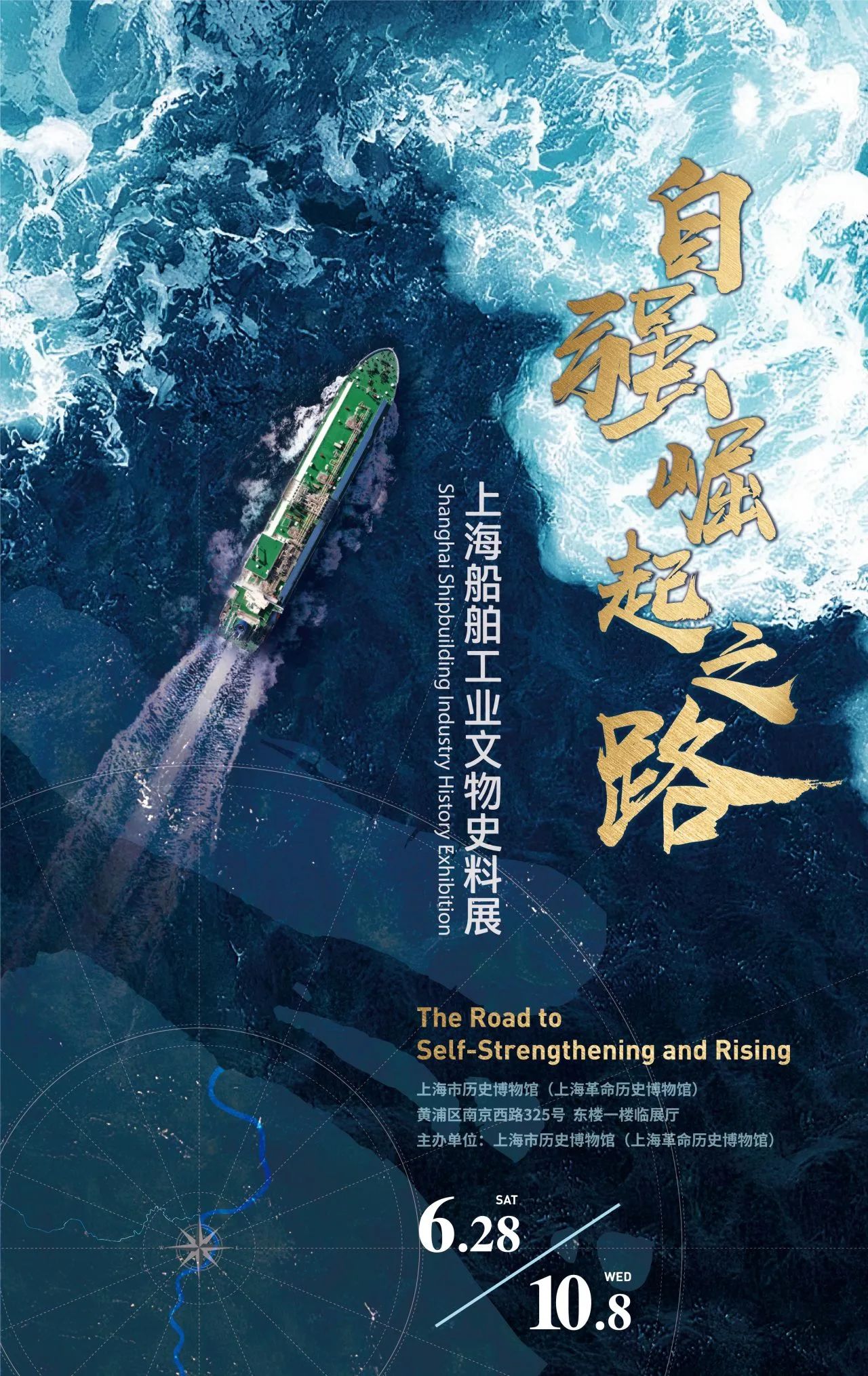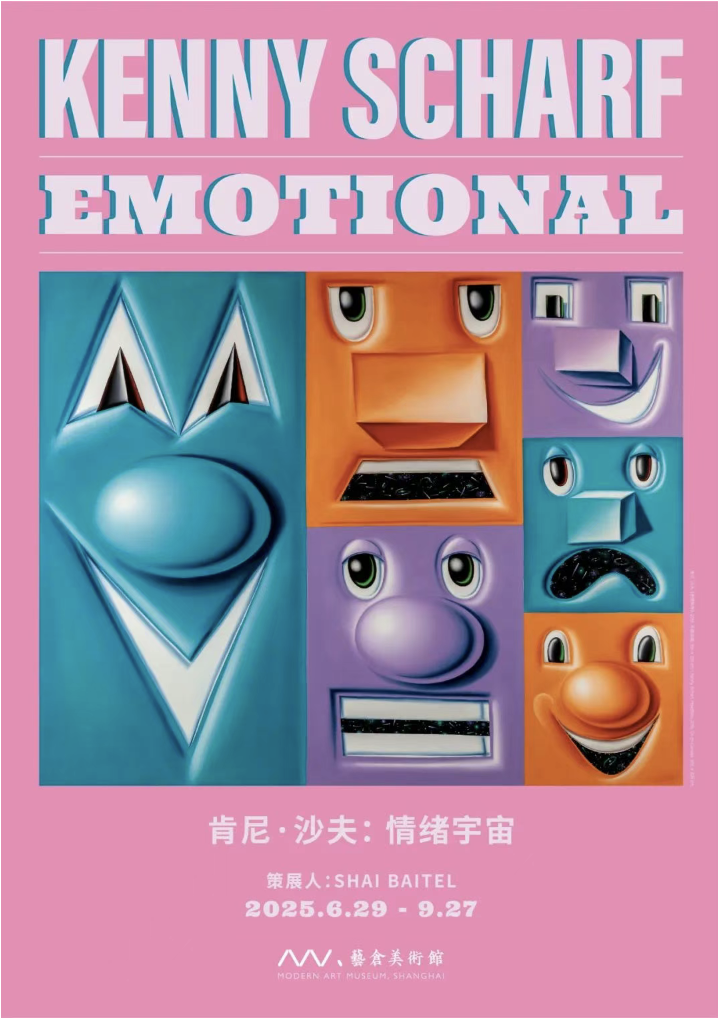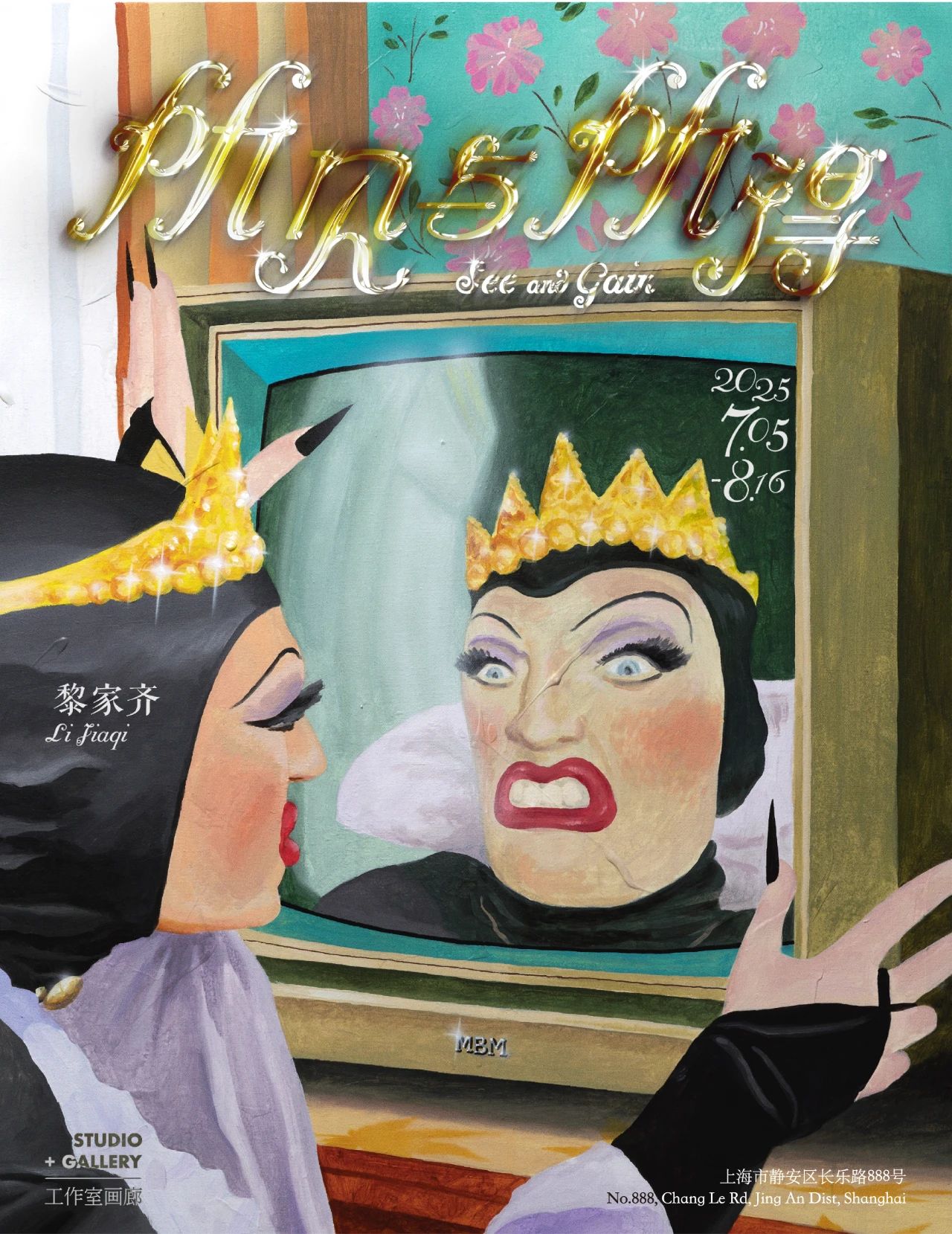中国艺术史是一部以文心为支撑,以文人为主导的历史,文人绘画在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既标志着精神修为的高度,又意味着语言推进的历史进程。近世以来,集学者与画家于一身者并不少见,如黄宾虹 潘天寿 傅抱石,既是美术史学者,又是绘画大家。新时期以来,于实践理论两端均有建树的学者型画家,日益成为当代美术界的重要力量。
作为成果丰厚的学者,晓凌院长多年耕耘于美术研究和教学上,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多年,桃李满天下。在理论研究之余,晓凌先生与其弟子们坚持绘画创作,勤于思考,不断探求绘画之道,取得骄人的成果。
此次展览主题为“艺道日新”,其义深宏。《礼记•大学》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在推颂革新,澡雪精神,以图发展。毋庸置疑,参加此次展览的画家大都是美术史论研究者,从导师晓凌先生那里,他们逐渐领会了理论研究的方法,形成了严谨的研究风气。然而,在艺术创作上,他们却又散发出活泼的个性。我们可以从晓凌的作品谈起。在这一系列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创作中,他以沉厚深沉的色调将炎黄子孙的历史与沧桑表现出来,在血色苍茫的大漠景象中,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脉动似乎就在眼前,令人油然升起一种“长歌当哭”的悲怆和豪迈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立红 李昌菊的油画静物,前者注重色彩的醇和协调,后者则极力营造出一种朦胧的“禅境”。同样表现禅境的是陶宏的“佛像”系列和葛晓成的抽象系列,前者将佛像置于天地之间,以当代绘画语言构建出一种新的图式和精神;后者则以阔大的笔触和明丽的色调,构成具有写意趣味的氤氲空间。
此次展览国画写意作品题材更加多元,诸如刘玉泉 吴洪的花鸟,魏广君 白宗仁 董雷的山水,王艺 杜少虎 陈明的人物,都体现出新意。刘玉泉的花鸟笔墨纯熟宛丽,吴洪的墨竹格调气清韵逸;魏广君的山水墨色精微厚重,白宗仁的山水笔墨淋漓酣畅,董雷的山水用笔疏旷清秀;王艺的简笔高士风流自然,杜少虎的戏曲人物质朴有趣,陈明的红衣罗汉古拙率真。就笔墨语言而言,这些画家都脱胎于传统,但显然没有受到传统的束缚,比如魏广君的山水(包括墨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图式,从中隐约可见印学所带来的影响。白宗仁尝试泼墨泼彩的探索,构成浑圆流畅的风格。王艺笔下的人物有漫画的趣味,这种趣味结合飘逸的行草,形成了谐趣横生的画面效果。刘玉泉和吴洪的花鸟笔墨不离传统,但却体现出个人化的格调。董雷的山水注重山形之方折味,从而生发出顿挫硬坚的新趣。杜少虎简化了戏曲人物的形象,以笔带墨,笔墨交融。陈明的喇嘛和罗汉引入西法,追求形神的相互映发。与其他画家不同的,刘立宇是玻璃艺术家。她将古典意象巧妙地植入玻璃艺术中,将其重构为新的视觉奇观,其作品澄明透彻,如诗如歌。
晓凌的夫人潘映熹作品也参加了此次展览,潘映熹受教于杜大恺先生,于油画 中国画皆有造诣。此次展览的荷花小品,荷芭鲜泽,枝叶挹露,一派清冽华光之景象。
《荀子》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晓凌先生与弟子们的展览,体现出传统师道的深意与魅力,也体现出他们于艺术之途跋涉的探索精神。在当下世风浮躁的环境下,这样的展览值得推崇,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