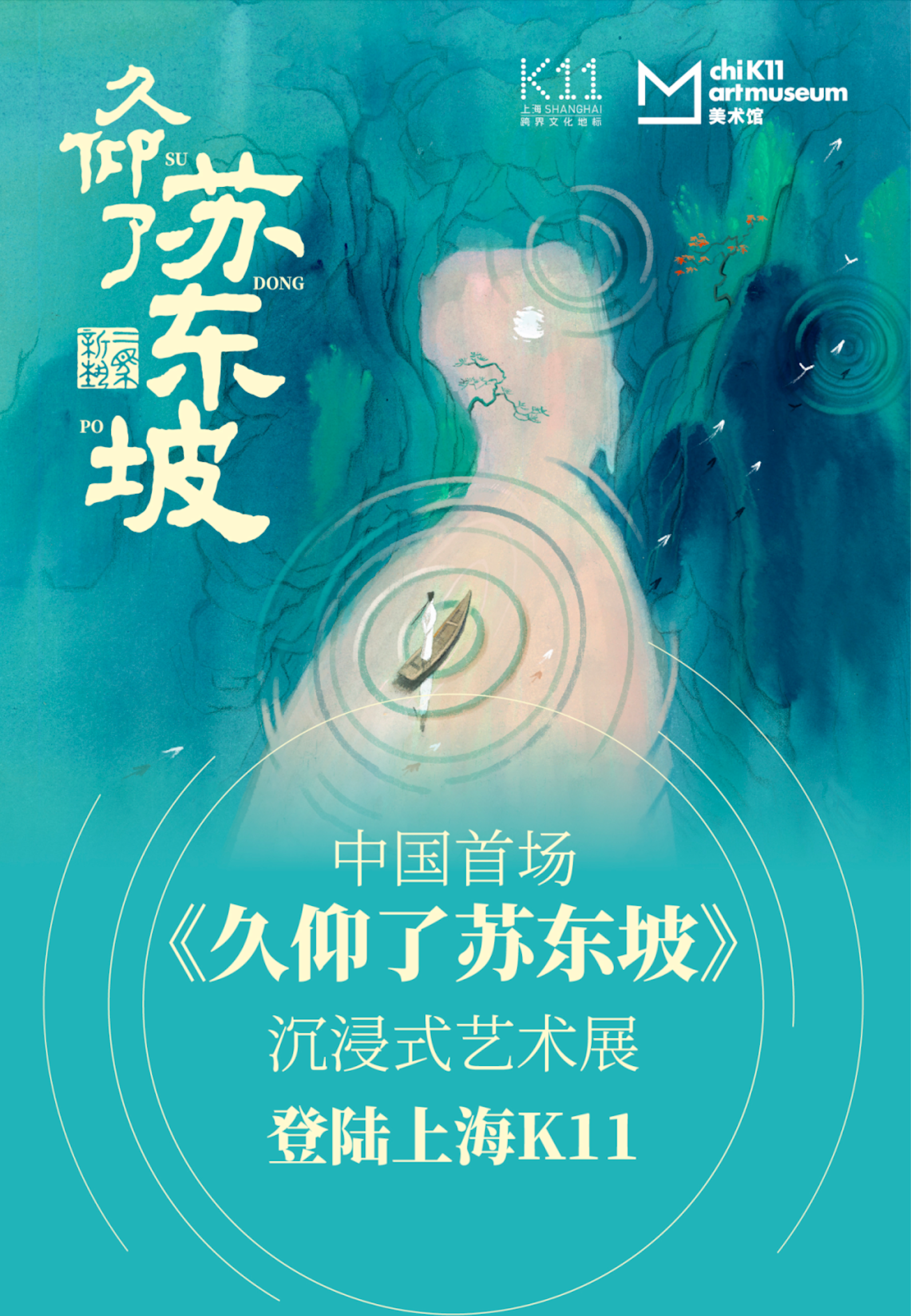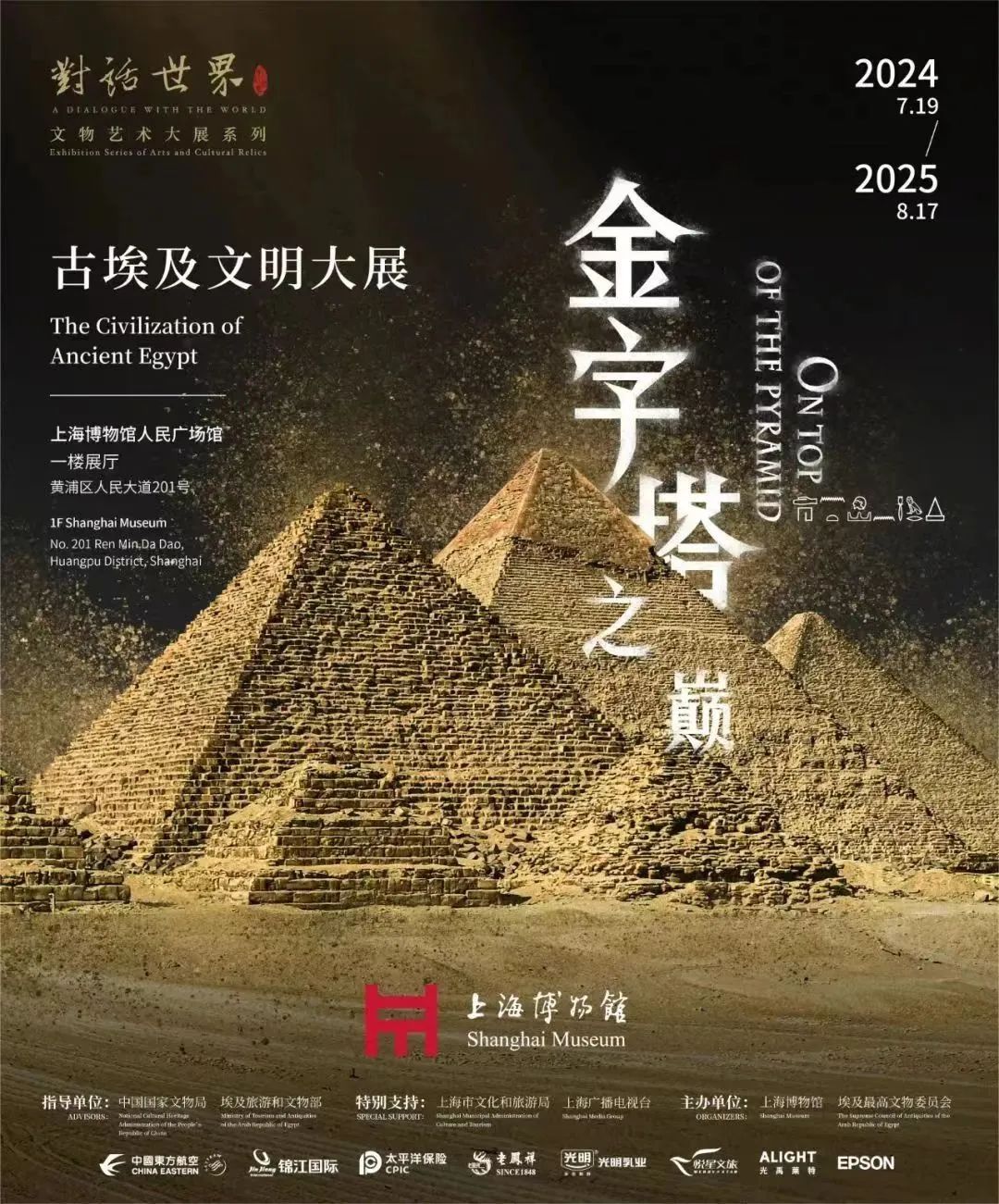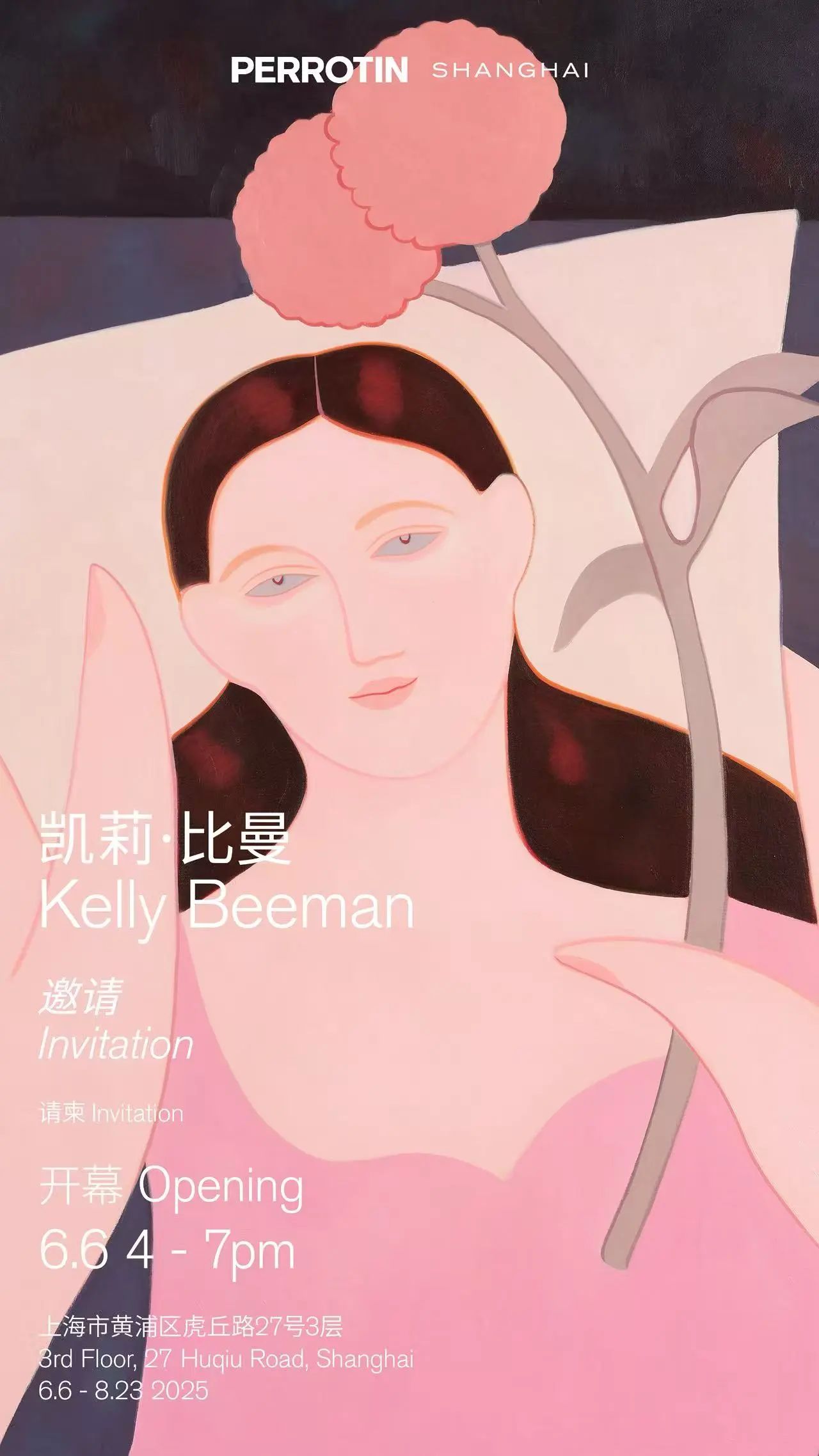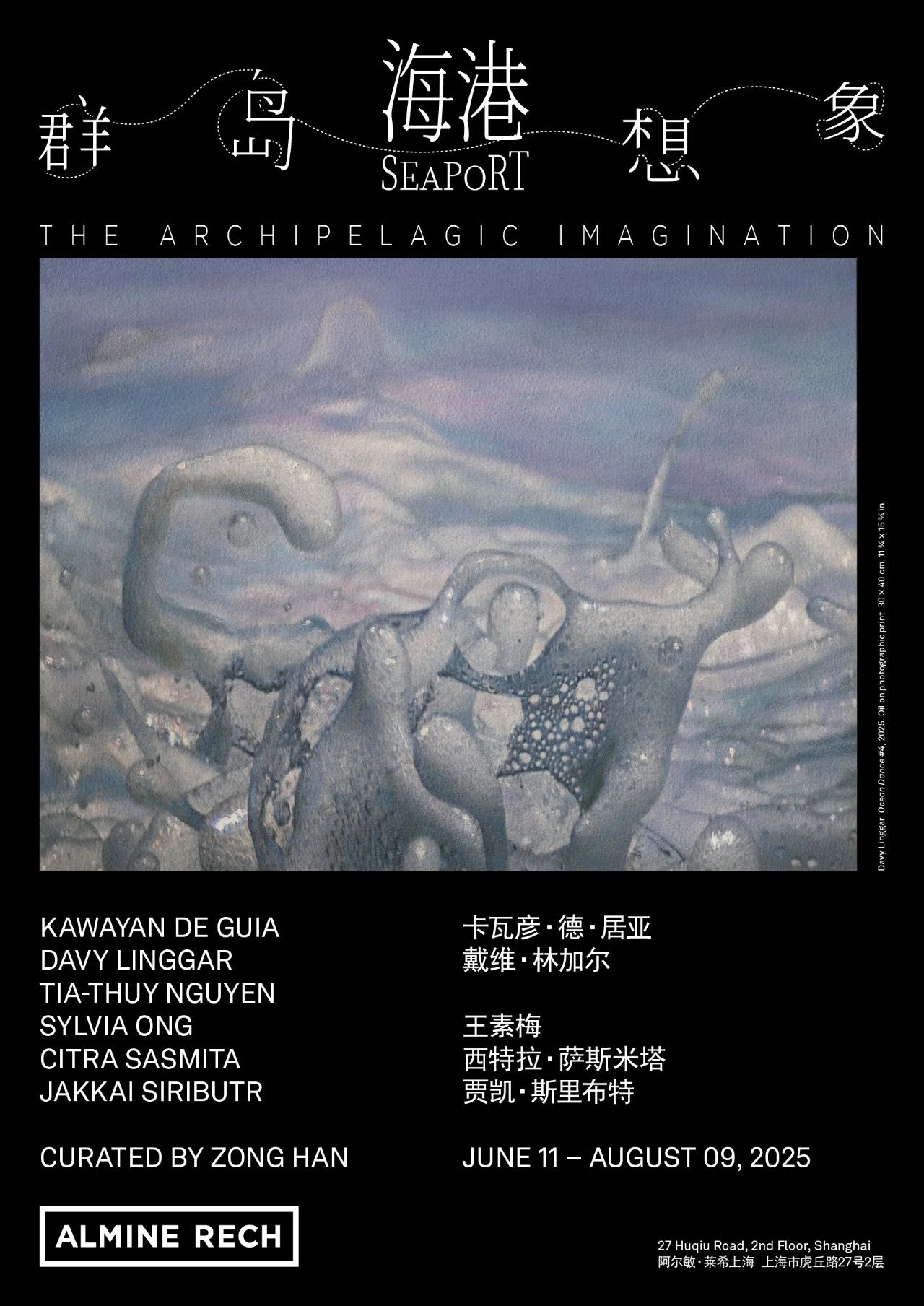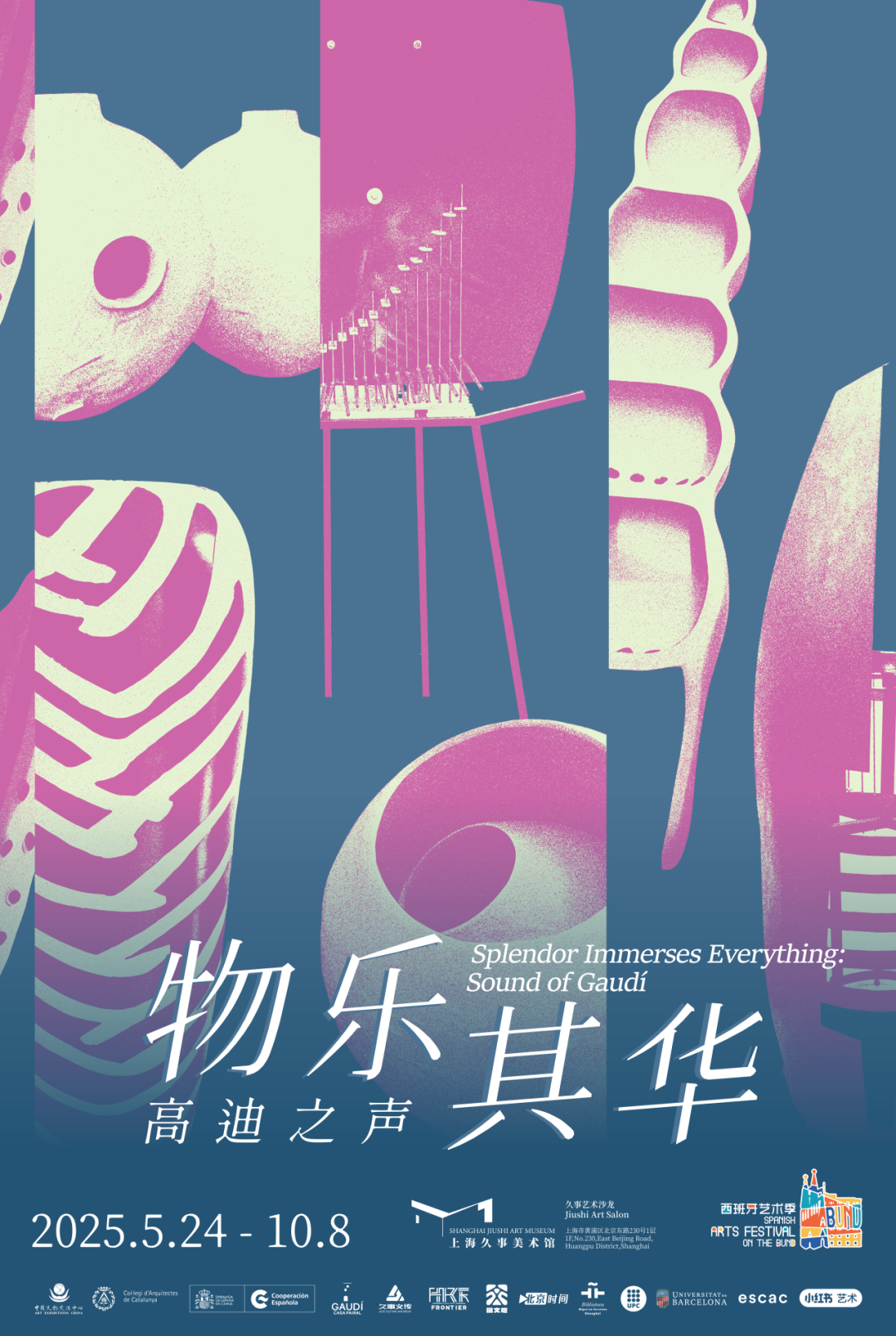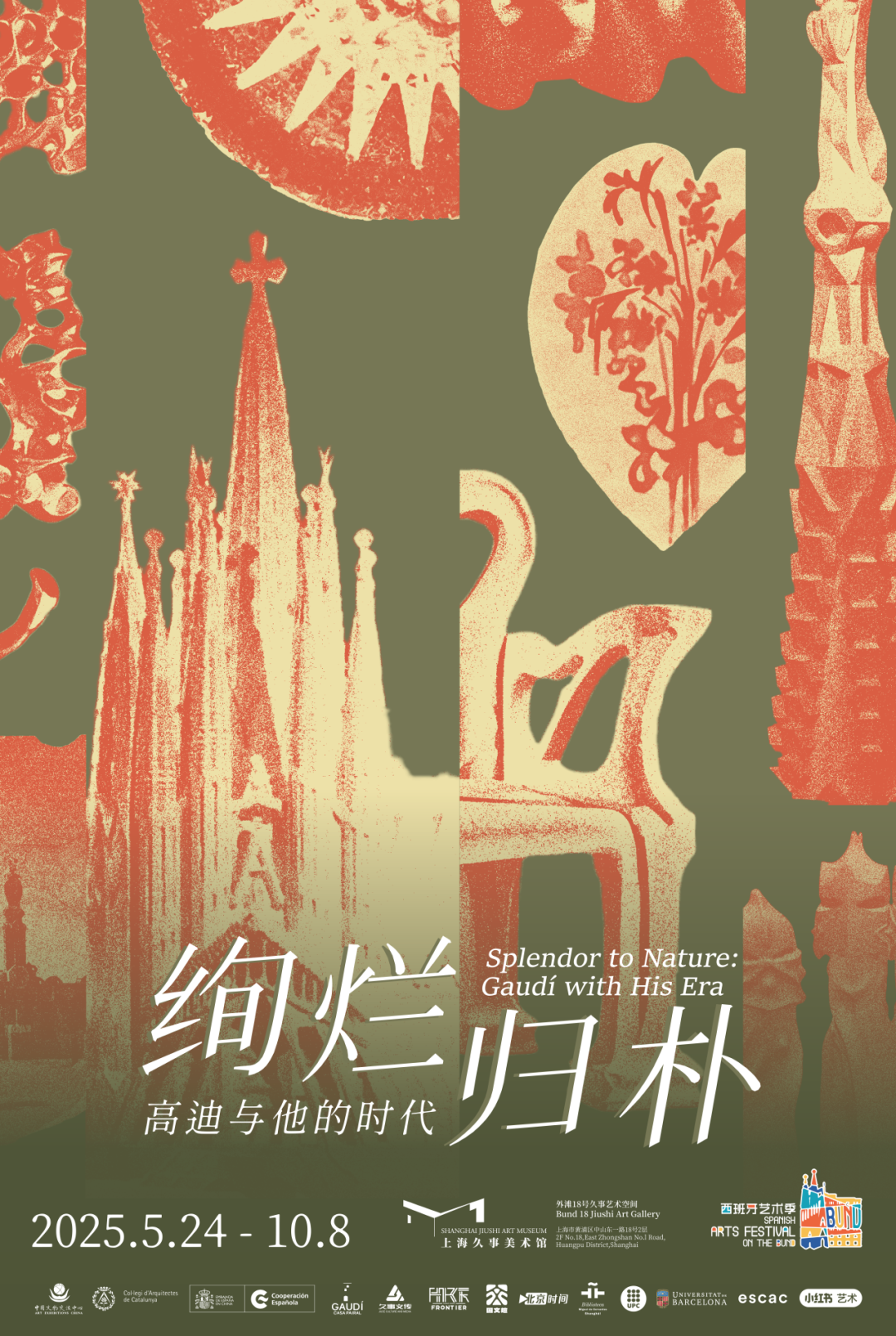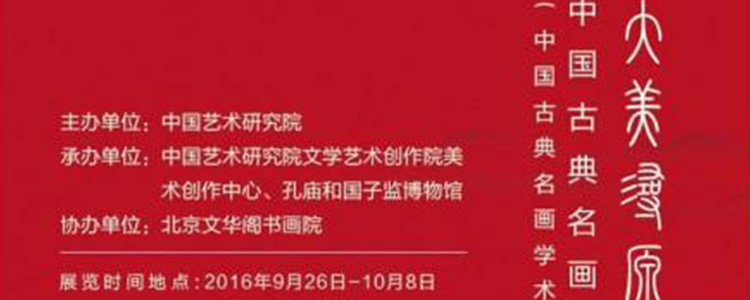
大美寻源·翰墨薪传——中国古典名画临摹暨国子监写生展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美术创作中心组织的系列艺术展览之一。与以往不同,本次展览我们将临摹、写生两个单项活动安排在一起,就是想“寻”中国画创作之“源”,通过展览进一步体会临摹与写生的关系及中国画创作中的“方法”、“观念”、“精神”等问题,并以此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方法”。在国画创作中,需要具备的条件有二:技法手段、素材内容。国画向来重视传统、与古为徒,在技法手段的习得上,除了名师指点,主要由临摹来承担。临摹虽不能脱离具体物象,但物象并非临摹的主要目的,它更多地侧重技法手段方面,诸如人物的线描、山水的皴法、花鸟的晕染等,无不依靠临摹来习得。画坛关于国画的“笔墨”问题争论已久,我们仍然认为“笔墨”是国画技法的核心,倘若脱离此一手段,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审美价值等内容皆无从依着,赵子昂的“用笔千古不易”确为圭臬。写生则是获取素材内容的重要手段,在创作内容方面,国画历来亲近自然而远离人事,以描摹自然物象为常规,故山水、花鸟为绘画之大宗,此类内容在题材方面的开拓往往借由写生来实现,纳自然入画图的做法较为常见。此外,写生所得也并非不能转化为技法手段,董源以江南山水得披麻皴、范宽以华山风貌得雨点皴,都是借助写生转化为绘画技法的典范。
“观念”。临摹与写生不仅仅是技法习得与素材获取,更反映了我们对于绘画创作的观念认识。就传承层面而言,临摹接续着国画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由国画之技法、审美、价值等内容所构成,历代的伟大画家无不主动投身于这一传统中,并经由这个传统获得自己的历史定位,形成一种链条式的“谱系”。此点对于今天的创作尤有启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若置身于传统之外,则难具创作上之存在价值。另一方面,传统既是滋养,也会成为束缚,例如晚明之后笔墨的陈陈相因。写生则成为冲破传统束缚的最好方式,那些名师大家往往又从自然万物中,获取一种鲜活的个人经验,他们认识到这种自然经验对于丰富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有效补充,可以避免因纯粹技法层面的陈朽不堪。今天,我们对于写生内涵与范围的认识较前人有所扩大,举凡现代都市楼宇、人情百态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写生对象,这些都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写生概念的观念认识。
“精神”。临摹与写生最终归结为对于传统“精神”与自然“精神”的把握。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说“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这文化传统与天地万物中的“精神”正是一种“常理”,殊为难得。我们认为,首先要对传统、对自然怀有一种谦逊态度,不是“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让传统和自然真正摆脱“我执”而回归到如其所是的位置上,使真“理”自现。此外,还应具备一种研究态度。临摹与写生并非是即兴创作,而需要严谨理性,边临摹写生边思考研究。例如,宋代宣和画院向来重视对景写生,师法自然,符合物理,以客观研究的态度,把握对象的“情态形色”,故能形神兼备。此一做法,正与宋人理学的“格物致知”相表里。至于“自然”精神蕴含着时代精神,原因在于我们是以时代眼光去观看自然天地的,诸如“新金陵画派”的傅抱石、钱松岩、宋文治、魏紫熙,正是以时代的眼光观照自然,创造出一大批以写生为手段改造传统山水画的优秀作品。
此次展览的作品分为三类,临摹古典名画作品、国子监写生作品、变体创作作品。临摹作品中,既有宋元山水,也有明清花鸟;既有几十年前的旧稿,也有近日新作。无论如何,这些临摹作品能够充分表现出画家们对于传统技法的刻苦和熟练,对于传统审美意趣的领会和把握,对于传统精神的体悟和传达。写生作品以国子监为表现内容,通过这一集中的题材,能够看出画家们对于素材选取、技法表现、情感表达的主体差异,正是在差异性与多元化中透露出国画创作的勃勃生机。
我们常说国画创作要遵循“师古人”、“师造化”、“融汇贯通”三个阶段。“师古人”为临摹,“师造化”为写生,“融汇贯通”则是在临摹、写生的基础上“迁想妙得”的创作,创作要以临摹与写生为基础。临摹写生是手段,创作才是最终目的。
从师古人之迹,到古人之心,进而师造化,向自然学习而达到自由创作境界。这是中国画继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展览第三类是变体创作作品,正是以临摹与写生为前提的艺术创作,这些变体创作移取了传统作品中的某些图像元素和技法手段,根据写生或生活经验,重新进行画面结构上的组合搭配,从而获得了一种既“古”又“新”的独特效果。
我们的一系列展览都以“大美寻源·翰墨薪传”为标题,正如上文所言,“源”是“临摹”与“写生”,在这“源”的基础上,我们的翰墨“创作”才能真正“传”下去,这正是此次展览的重要意义所在吧。
——杨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