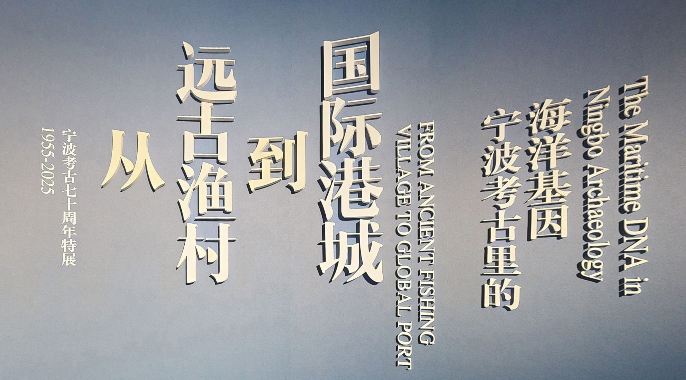画有画理,有物理。对于表现对象的“物理”,或者不可不讲,或者竟可以不讲,然而画理则终究不可不讲。画理牵涉到材质的应用,因此,绘画具体到某种形态,则作为物质依托的工具材质等物,又必然包含着“物因其性而用之”的“物理”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讲,画家欲明究画理之本源,不仅需要明究其之所以如此的文化属性,亦须明究其之所以如此的物质前提。
人有感慨,而后有诗意。诗意在心胸,有不必向人道者,有不能向人道者。因为要借一种诗学的语言道出,于是就有了诗文书画歌曲等文艺形式的发明。所以说诗意的存在,本不在诗学成立之后,而在诗学成立之前。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韩愈说:不平则鸣。苏东坡说: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今人动辄喜欢引用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道是:愤怒出诗人。
书画是寂寞之道。这不仅是指作书作画要耐得住寂寞,坐得起冷板凳,更重要的是,书画本就是寂寞无可如何之境中的无奈心绪之感慨,无聊衷曲之发抒。艺术家固然需要深入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更需要脱开生活的牢笼。艺术的表达需要适当掌控与生活之间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不即不离”。对此,王国维发挥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写”与“观”是艺术创造的双翼。“写”主动,“观”主静。“入乎其内”固然需要艺术家拥有一颗对现实世界足够敏感的心灵,而“出乎其外”却需要艺术家对艺术形式的符号世界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实践。“入乎其内”可以是人人皆有的情感体验,“出乎其外”却非远离一般人群的惯性思维不可。前者重在集体经验的通感,所谓“四时佳兴与人同”是也;后者重在自我视角的设定,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是也。由是,我们不妨说,艺术家其实是生活在两种类型的空间里面:一种是和普通人共存的那个热闹的空间;一种是只为他自己而设的独立的空间。从前一个层面上讲,是“笔墨当随时代”;从后一个层面上讲,是“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没有了那个热闹的空间,艺术就失去了思想的源泉,但若没有了那个孤独的空间,艺术的创造活动也就不复存在。
在画家的身份认定上,中国古代没有“画家”与“非画家”的分别,只有“行家”(专职画家)与“利家”(业余画家)的分别,甚至认为“利家”的境界高于“行家”。赵孟頫曾向钱选请教说:什么是利家?钱选告诉他:不要把别人的评论当回事。董其昌把这句话奉为经典,但听到这话的人几乎无不皱眉:此关难度啊。古人作书作画,每喜题上“工拙不计”的谦语。这并不是说绘画真的可以不计较工拙,而是说抱着患得患失的心态进入创作,先就在未画之先输了一着。从一个意象的兴起到此种意象的落成,艺术创造的过程容不得半点牵强,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隔”。
赵之谦论书,以为古往今来惟两种人可当真书家之誉而无愧:一是三尺童子,再就是通学大儒。三尺童子,初学执笔,胸无尘滓,一片天真;通学大儒究竟通透,空明廓朗,了无挂碍。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其实,论书如此,论画又何尝不是?所谓原生态绘画、儿童绘画,之所以在现代艺术场域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皆因为其以同样极具生发性的创造活力影响了人们对有关绘画本质的根本态度。原生态的概念虽晚在二战以后才由法国画家杜布菲提出,但原生态绘画却无疑自人类绘出第一张“绘画作品”始就已经存在。从本质上讲,儿童画也属于原生绘画的一类,儿童画家与原生画家每于不自知中流露了天真的本性,不造作,不逢迎,直探艺术的本源,因而呈现为艺术场域的开放状态;而作为一门“专业”的绘画起源于人们对绘画的自觉,画家往往自觉着绘画的行为而不自知、不自省,由是反而容易落入绘画为自身设下的陷阱。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画家若不能做足诚心敬意的功夫,放下事事循人的媚态,就很难从绘画自身的陷阱中脱身而出,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创造活动,绘画由是也就沦为技巧的奴隶。
“媚”有“媚俗”,有“媚雅”,“媚俗”固然万万不可,“媚雅”同样需要警惕,因为两者并不具备本质上的分别——它们同是丧失自我判断的结果。艺术最忌讳的就是“撞脸”。然而“撞脸”也有自觉不知觉之分。画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是选择主动趋避还是迎难而上?恽南田与好友王石谷山水风格相近,因为“耻作天下第二手”,最后竟改作没骨花鸟;倔强的石涛则大言炎炎地说:纵使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非我故为某家也。对于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画家而言,恐怕任何一种选择都不难寻出足够充分的理由,亦不妨其人臻于高妙的艺术境界。
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就势必面对“和葱和蒜卖街头”的尴尬命运。雅俗之分是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价格高低却是市场博弈的结果。画家作画,最忌患得患失。与其抱着“下调无人睬,高心又被嗔”的逢迎态度,倒不如就以“诗到无人爱处工”的决绝态度摆明自己的立场,一意孤行地做去。从根本上讲,在画家看待艺术路向选择的态度背后曲折隐映出来的,仍然是其各各不同的人格魅力。大规模的无声淘汰是艺术史的常态,而鱼目混珠却是市场的常态。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有错位,有交叠,甚至有背离。世俗论画,首先认名头,其次看画工。画家既无名头,又无从分别优劣,则往往以尺寸大小、画工若何计算其商品价值。殊不知画有工粗,是体格之分,不必与作品的艺术价值作机械对应观。精雕细琢者自当以“见工”为能事,乱头粗服者亦不妨以粗率的稚拙为高明,其价值又如何可以商品价值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
推动西方艺术史向前发展的是技术控与反技术控的二律背反。从古希腊罗马时期栩栩如生的雕塑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在二维平面中展现三维立体视效的明暗透视法的成熟,从由画家作为辅助工具使用的暗箱到摄影、摄像、电子数码技术的发明与革新,模仿说作为西方艺术发展的主线始终以变换着的各种物化形式介入并影响着我们的观看方式。反技术控思潮的崛起源于西方近现代社会学家对人的异化现象的深刻反思。如果说印象派在貌似感性的挥洒背后隐藏的是对光色原理近乎顽固的执守,后印象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冷抽象、热抽象对画面形式自律的探索,达达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对人类无意识之梦的执着往往受益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而现成品艺术、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出现则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强势崛起息息相关。
古人云:怒气写竹,喜气写兰。达芬奇说:绘画是一门科学。中国画更多强调画家情绪投入对绘画形式表现的决定作用;西方绘画则更加专注于借助透视、解剖等相关支撑学科来设定相对明确的量化指标。从操作体验入手介入绘画的观照方式催生了中国人从创造主体所处综合情景出发对评骘标准进行灵活调控的掌控原则;从关注视觉生理、心理体验介入绘画的观照方式则催生了西人从观者角度出发来思考、建构、改造绘画语言的美学原则。二者从各自元点出发构建绘画本体的路径之差异造就了视/知文化与体/认文化的性格差异,其间虽不乏某种视觉甚或心理层面上的交叠,但毕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鸡蛋。而哲学家莱布尼茨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不存在性格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因此,从理论层面上讲,即使面对同一颗鸡蛋,在不同的画家那里也存在着无限种表现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母题在不同的画家那里常画常新,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仍能翻出新意的关键所在。对象世界多样性和主体精神差异性之间存在着无比丰富的组合、对话之可能。对于绘画而言,“表现什么”的问题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如何表现”。正所谓“有一千个观众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物无论新旧,人无论古今,画无论类属,画家倘恒能于情感投入和画理物情的内在关系上着力,也可以称得上是“思过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