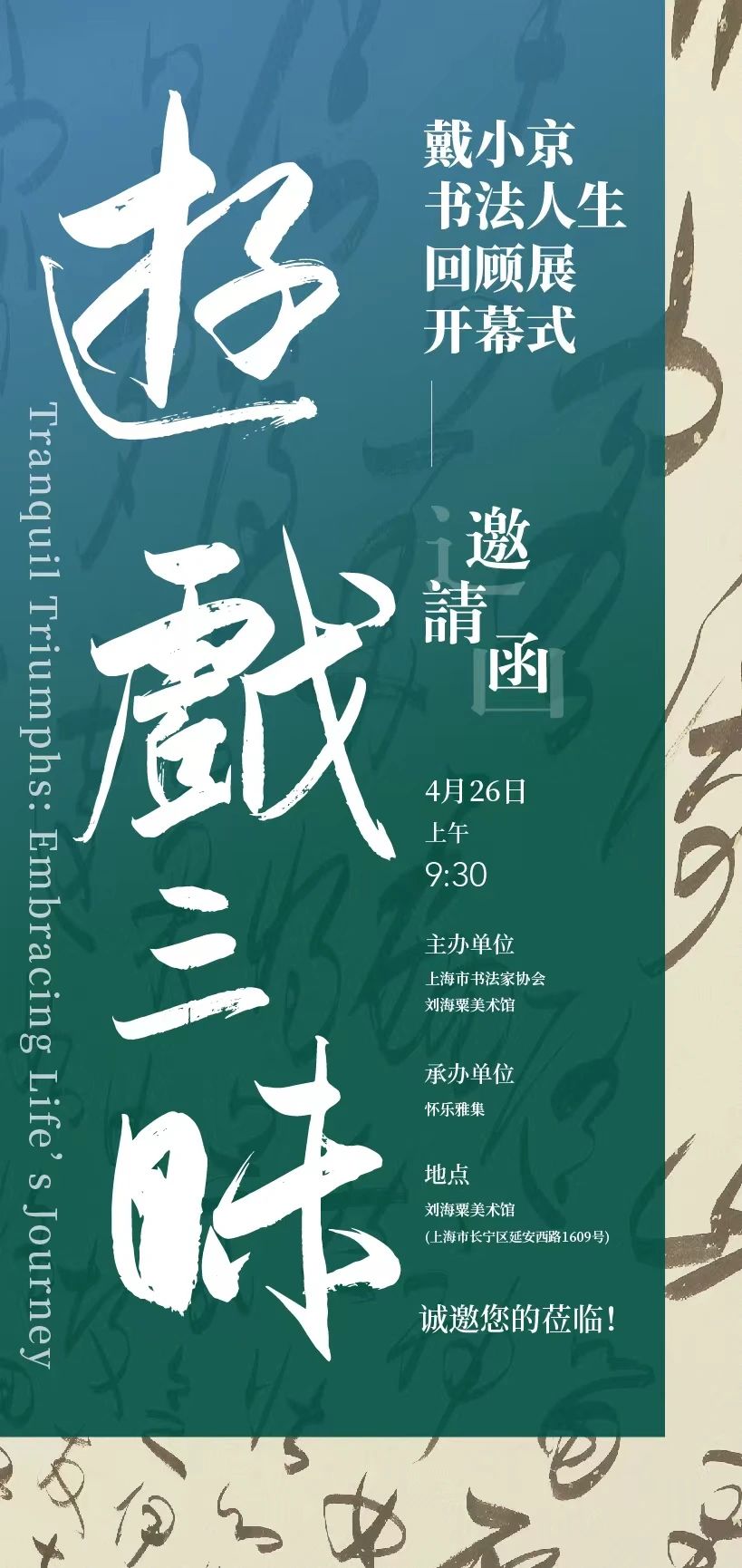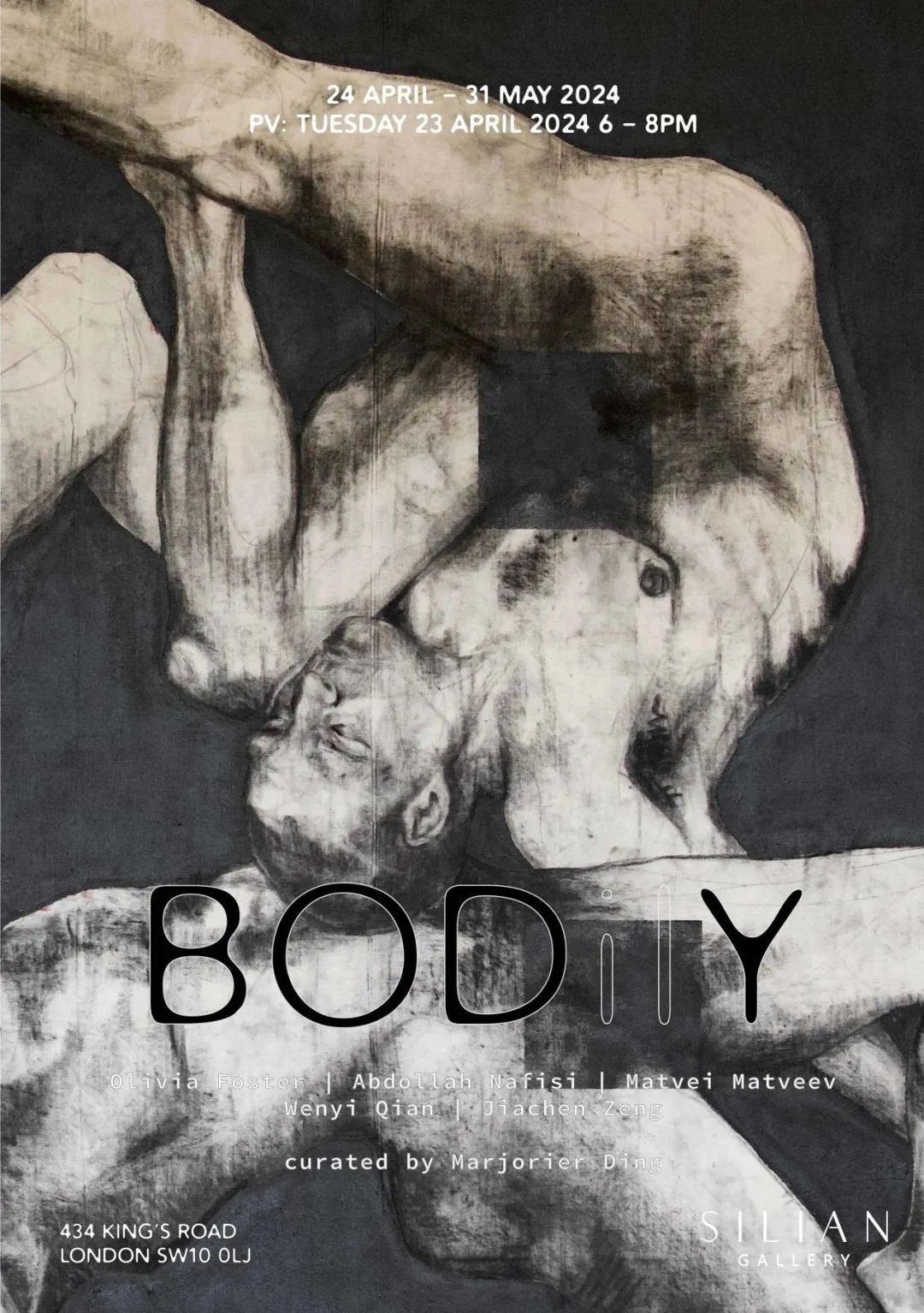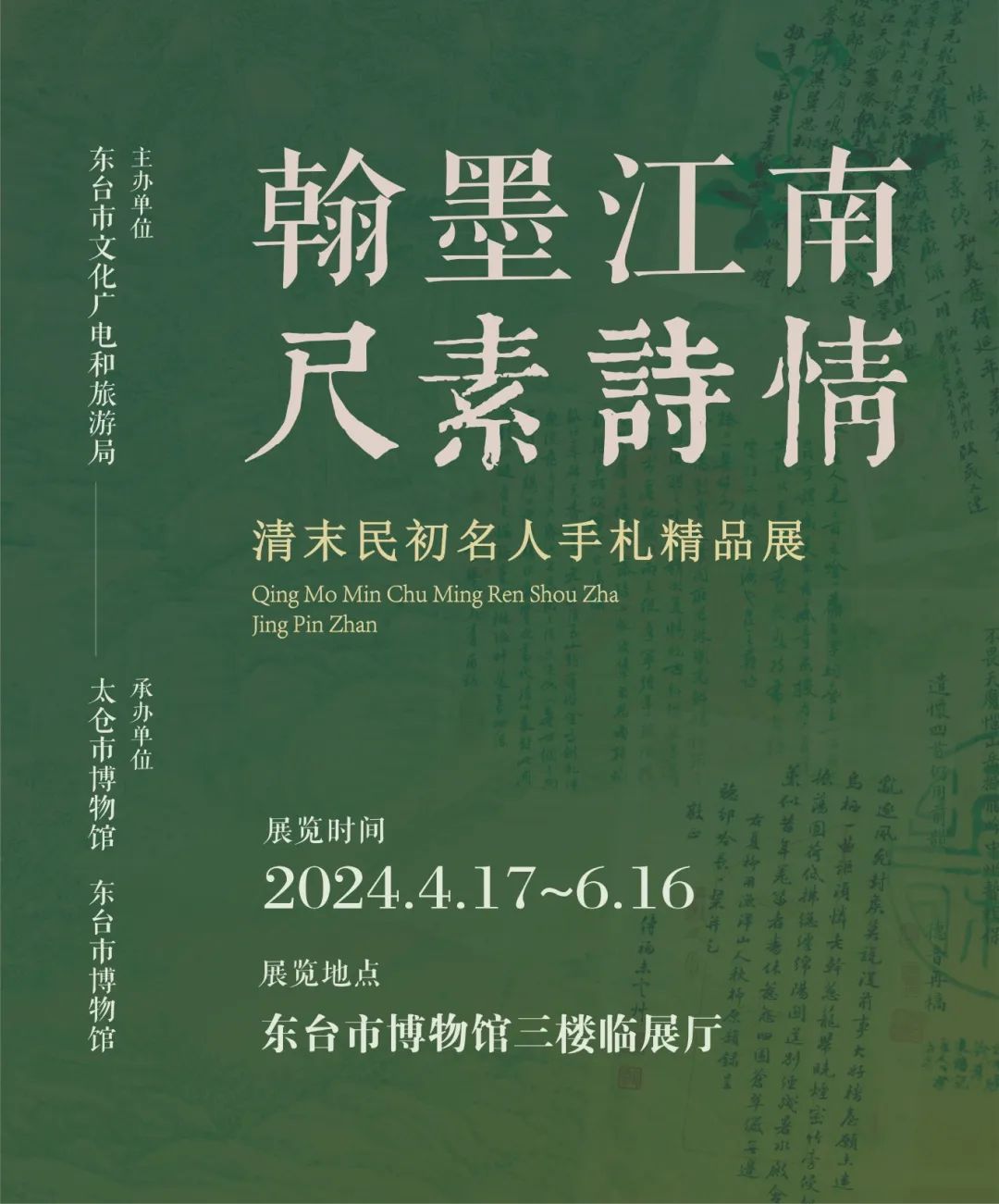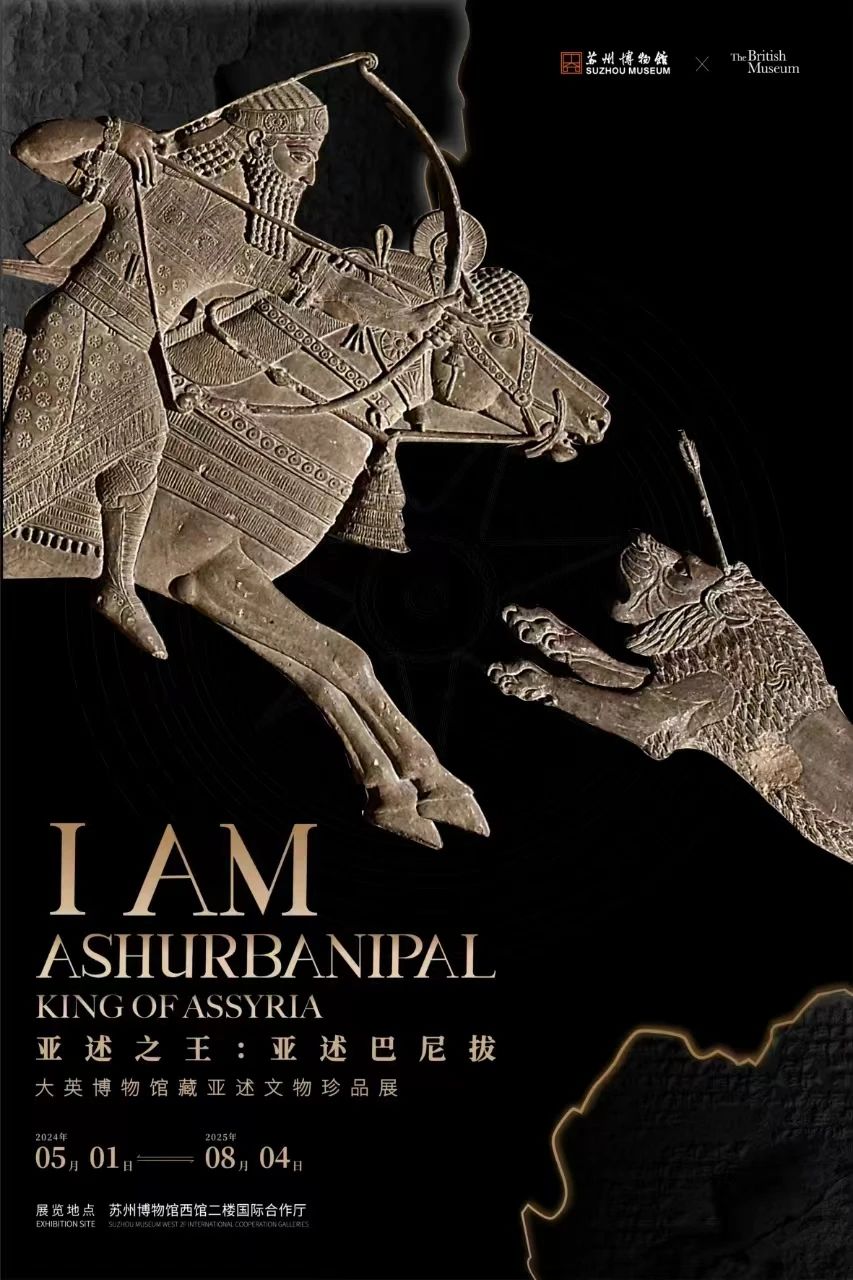内在的神圣——董重绘画中开放的精神向度
宣宏宇
董重的绘画向来都有一种原始的神秘感,它们大多包含着含混的叙事性,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形象组合常令人联想到洪荒时代的神话。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语意层面的偶然关联,若细细品味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指向另外一个更加深层,以至于不大容易被意识到的精神领域。或许,关于这个领域的艺术表现早已为某些现代主义艺术流派所涉猎,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但其中的艺术表达总是明确地指向某种既定的信仰而非开放的个体精神体验。
作为一种强烈的信念,早期的信仰源起于生存需求,如原始崇拜。按照艺术发生学中证据颇丰的一种观点——巫术说,艺术恰是从原始崇拜的仪式中获得最初的感官形式,这些形式通常都有着高度的神秘感、稚拙感和概括性。后来,它们被不断丰富,生出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并在宗教信仰中形成为某种符号体系。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有着多么丰富的类型,但总的说来无外乎两种向度:其一,为着生存,即关乎人的实际存在问题;其二,对生存意义的解答,即人的最终归属问题。
董重的作品在感官形式方面同前者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它们显然并不是为着实际生存而来的某种灵媒;同时,它们也没有试图探讨人的最终归属问题,甚至也没有宗教信仰的严肃性。相形之下,它们更像是一些戏谑的趣味性图像,但却又流露出一种莫名的庄严感。它不指向外在的鬼神,而是内在的神圣,是个体对自身由来的深层追问。
在最近的一篇随笔中,董重讲述了一个“飞头人”的故事和梦境,这个故事源起于一则岭南的地方神怪传说,而梦境则是随着听过这个故事之后而来的。在故事与梦境中间的时段里,董重曾试图把“飞头人”画出来,但因结果“不如人意”只好作罢,继而却让梦去完成了。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或许可以建立一系列意识与图像的对应关系,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标识系统,无助于理解其间弥散出来的内在庄严感。
实际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少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董重的画和他的梦也是这样。相反,从他一路走来的绘画语言变化中倒能找到一些线索。从早期色彩鲜艳的梅花系列开始,到后来的鬣狗与“毛怪”,再到新近的场景式叙事,董重的绘画表述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图式到笔墨趣味再到戏剧性的变化过程,其中始终未变的是那种充满蛮荒气息的神秘感。在新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神秘感被坚硬的轮廓线切割成强烈的明暗对比,以至于其中并未被减省的笔墨细节显得十分低调,仪式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产生了莫名的庄严感。
或许我们曾在卡拉瓦乔的作品中体验过类似的庄严感,但那是一种有着明确宗教意味的庄严感,它包含了太多的集体经验,加之那些对应着经书的具体典故,显然太过具体了。董重作品中的庄严感恰恰相反,一贯含混的意义丝毫没有因为形式的分明而清晰起来,倒是荒诞语意与生动情节间的冲突让其间的庄严气氛愈发地晦涩。
同时,这也不是达利的《记忆的永恒》中的那种晦涩,那种晦涩充满形上之思,许多意义明确的符号似乎是在设计一场解迷游戏。董重的作品不是解迷游戏,它们更像是黄昏的夕阳,究竟是伤感还是振奋只取决于欣赏者的状态。因而,它们是私密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它们打开了一个感官之门,任由观者漫游于其中,而专属于每个观者内心深处的神圣感即由此得以生发。
正如我们最初的感受那样,这样的视觉游历在某种意义上与蛮荒时代的先民有着极高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董重绘画所激发的内在的神圣无关于生存,而是生活的追问,并且它朝向过去而非未来,是对个体对自身由来的再意识,信仰在这里真正成为个人的事,就像董重在耶路撒冷的感悟:……这时我有些明白了尼苦拉双手托起仰望星空,他是真真正正看到了他的神,他也指引我,让我能看到我不相信的神……嬉皮笑脸的我,只有把艺术当做拯救自己灵魂的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了。